吉玛除去长裤。白而透洁的疣,树瘤般直直攀爬双脚。吉玛从头到脚,像一道由暗红至白的渐层色阶。他发现吉玛没穿鞋,脚边扩散透明,带水气的光。就在吉玛要褪去内裤之际,他醒了,抬头,暴雨已歇。他左右松转僵硬的颈部与肩,走出地下道,水色月光相织的蓝浸泡了整座花园,像吉玛走过的痕迹。
有人穿梭树丛里,他将花园,台阶,地下口等所有细节纳入眼底,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了。空气凉爽,夜空下他伸手道别,他拔腿奔跑,决定今晚将熟睡妻子身旁。
睡前,他从厨房抽出利刃,并于水桶里注满半桶冰块。他在澡缸前依序剥光自己。围巾,旧牛皮外套,白衬衫。他褪去内裤, 左手持刀,紧闭双眼。许久,低头看,却是一整面光滑,新生的皮。他不信神的,但那晚,他闭眼,跪在浴室冰凉的磁砖地,蜷起拇指食指中指,在胸前,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画了十字。
隔天他特地早起为妻子备餐,不善厨艺的他,只简单地将冰箱底层的马铃薯洗净,去皮。锅底先热油,他倒下切成长条状的薯片,最后在煎至金黄的焦面上打了两个蛋。
特地绕至街口,踮脚,他摘了几株金合欢花插在桌上白瓷瓶里,他满足地看着一切,并在胸前画了十字。他将更换时区,与先前永夜的自己,切离。妻的笑声打断了他。他回头,满足地看着妻,虽然他还无法直视妻的脸,但他学习将眼神对焦在她的肩,颈或髮梢。出门前在包包里放入备好的麵包,他在妻子的脸颊上亲了三次,便哼着歌走上街。
城中大道,一辆车疾使而来,将他锁入另一段永恒的黑。
结束绵延话语的他极渴。
空白磁带仍在密室里嘶嘶摩擦着,他却再也挤不出一丝口沫或词句。桌上放一只沾灰玻璃杯,他觉得这摆饰,多少带了点恶意或玩笑。 他将脸颊平贴桌面,用手指轻轻敲着,单调的音。
他想,这时刻,该有多少人与他在相似处境做着同样动作呢? 他继续敲着桌面,单音,双音,单音双音,快慢,慢快,像组传递,连结无线黑域的密码。
脚步声在他身后聚拢,睁眼,队长再度位于前方。
队长拿起录音夹,按下倒带键,被压缩过的声音蛇般窜出。队长满意地点头,并递给他一张白纸与签字笔。写下那些记得的姓名,就自由了,队长说。他迟疑了一下,擎笔,从记忆洼缝中掏出那些相关,与不相关的名。
临走前,队长将一架旧电视机挪入室内,银幕上头,领袖翘脚,穿棉质运动服,舒懒地躺在沙发上受访。访者西装笔挺,正色问,关于许多人权组织获报,控诉您逮补并虐待同性恋一事,您的看法是?领袖皱眉,露出孩子气的笑。手抚肥美羊毛堆般的鬚,隔了一会,领袖摇头。
他们是不存在的,领袖说。你说的那个词,我无法复述,那种东西,是不存在这国家的。
他们释放了他,门拦旁,队长郑重地为他套上头套。他们这次温柔地,将他拥入车内,些许阳光筛过黑布,落入眼际。等头套被撤下时,他已身处家门前,他回头,男子们对他恭敬地行了礼,扬长而去。
他稍稍转动门,锁头便轻易滑落。屋内是一片狼籍,妻子的物品已被清空,还有那只皮箱,与他提早买的,昂贵遮棚婴儿推椅。
他在客厅为自己点了烟,缓缓地朝空中喷气。
好事的邻居早已在家门前探头探脑,说着细琐,像是安慰,解释,又像混了辱骂的词语。他想,很快城内所有人,都将知道他的事情。他用鞋尖捻熄烟蒂,走到巷口,为自己买了几桶漆与修缮工具。
整个下午,他用木板自组简易刨台,裁定一座等身大小的深色木柜。傍晚,他将整间房间与所有家俱刷上一层又一层黑漆。待月光洒入厨房,他关上灯,打开厨柜,把剩余的黑漆淋在身上。钻进橱柜,阖上门,双手环膝,他想,午夜来临,吉玛必随父亲,兄长们,从宫廷花园地窖最暗一隅,攀爬而出,擎着烈焰与刀,往他的家方向逼近。
嘘,不要出声啊,否则他们要找到你了,他对自己说。(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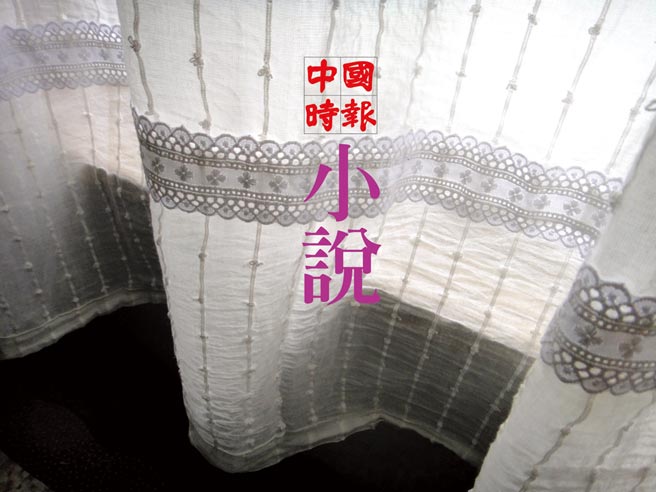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