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理解妻子。
她不去,其实我心底大概猜到她不会去,但这样是心有灵犀吗?我不理解的是,她如何变成现在这样?
来自公司的一个邀请,有幼龄孩子的同事们,要一起去个规划整洁而慎重的农场。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去过,记得主人不断告诫我们不要踏进水池附近,或是草丛里,他们正在復育萤火虫。
同事邀约时热情地说,好想见到你老婆喔,她想必是个很好的人。
我一直没回答同事,也拖着不问妻子。答案其实早就等在那里,妻子想必将回以冷漠的脸。过几天同事又问,我索性直接拒绝,同事看似失望,其实回头只在未确定的名单上划了叉,终于能确定预约人数。
妻子想要永远成为一个秘密,拍照录影的时候估量镜头的范围,躲到边缘,我自然就配合着,把她剩余的身体挪出去。偶尔想跟她端高手机自拍合照,她说她拍我就好,比较好看。她先从我所有影像檔案里消失,接着我成为社群媒体上无妻的育子者,她甘愿是一对窥视的眼睛,在镜头后面我和孩子拍下影像,或是跟着旁人一起旁观我的社群媒体。
她说她喜欢跟其他人以相同的距离望着我,自己则不爱被太多人观看,消失也没关系,连我的观看,她都觉得灼热难堪,习惯地闪躲到边缘,她计算我注视她的时间,熟练避开我的黑眼珠,我甚至不知道她何时曾专注地观看自己──化妆时仅在小镜里放大局部,衣柜里的穿衣镜是快门,取完衣服后就关上了。提到衣服,她衣服不多,每一周的样子是重复的,一整个月就模糊了印象,我们这么多年了,两个孩子,时间滑坡式骤减,记忆力也是,只记得衣裤似乎确然渐渐增幅拓宽。
斟酌过一天,我试着问她,她果然立刻拒绝,再说服她,为什么不去?刚好夏初,去看看当时谨小慎微的农场主人,将萤火虫復育得如何?
平地难见到萤火虫了,农场座落在市区近郊,山边水畔,能见到也是这时代的奇蹟。妻子摇摇头。
我觉得奇怪,记得小时候萤火虫就在身边,刚开始换穿短袖,风还带点微凉,皮肤带点裸露无可闪避的尷尬,家附近大水沟旁的草丛,平房与平房间未开发的荒地,甚至是电线杆旁的盆栽,就有萤火虫的绿光点点散飞,萤火虫不是爱乾净吗?不能随意践踏、入侵他们的栖地?周遭环境不能有过度曝亮的光?
我跟妻子说,以前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起约去小学操场跑步瘦身,接近深夜时,我追过操场中央草坪里飞出来的萤火虫。
妻说她不记得了,没看过,怎么可能。
我们那时候暧昧中,并肩着跑,分不清楚谁追着谁,我跑得长,她跑得短,可能时间太晚,她先回去了。
萤火虫发亮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当它们开始飞舞,就是成虫准备交配传承的生命末期。为什么以前处处是萤?为什么操场里有萤?而且仅见到一只,零零落落飞,闪亮起来,与谁竞争,向谁求偶?
在我们小时候,空污微尘还在远方,这些都不用担心,夏天一到,它就出现了,自然凑成一对,自然编织而成的家族树,同一个季节,另一个子代。
我们以前因为跑步都变得很瘦,新陈代谢是果真有在流动的数值,不用费心妆扮自己,便有天然散发的费洛蒙。她的头髮染黄烫卷,乾松,看得清楚每一根髮各自要去的方向,像当时急躁而活跃的她,头顶新冒的黑像一只手掌捏稳她的轴心。我的衣物极少,身上总没多少钱,头髮百元快剪后就任其生长,几件格纹衬衫就是最适合外出的礼节,裤子和鞋子以一两款深色耐脏百搭为宜。
年轻多事,人来去如流,眼光随意翩转,我们急着往彼此眼里钻,她常笑,偶尔习惯性地掩嘴,偶尔没有,笑的时候露出牙套,她牙齿小小的,箍上银亮的钢线,只看得见上方粉红色的牙龈,像一朵粉红色花瓣缀着白色花蕊。
我们能让彼此开心,看电影、吃餐厅,小旅行,合照互拍,说不停的话,在电话与讯息上继续,轻易地大哭、大吃、大笑,每天一起运动就是最亲密的约会。
我故作激昂地说,看萤火虫超青春的欸!妻子仍是执意拒绝。我想起一次带孩子去溪头赏萤,跟我们都相熟的朋友。导览员提出各种告诫,不能喧哗、照光,不能抓捕,以及随意走动穿越,不断警告我们萤火虫这样或那样会惊、会死,我心中困惑,萤火虫为什么如此容易死去?
趁空檔时私下问了导览员,他回答,那些干扰会让萤火虫找不到交配的对象,无法完成生殖的任务。萤火虫成虫后不再猎捕进食,仅吸点露水与植物蜜露,可能就这样澄净而孤单地度尽余生。
妻子说起不想去的原因,她完全不认识我的同事,这样子突然相见,当日熟稔,太奇怪了。
是她不再习惯社交,还是我习惯掖藏着她?太多陌生的眼睛是强光的连续轰照,我的社交与她完全分隔,她不在光下,除了孩子,世界变得很安静。她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年轻的她大方自在,不在意美不美丽,只追求能够尽情大笑。
不知从何时开始,她不吃饭,死命求瘦,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之前吃完了,总坐在一旁看着我和孩子吃。即使拆除牙套很久了,不笑,常瘪嘴,以至于嘴角放松时自然下勾,整个人被扯得重重的,像放在床上被压到变形的布娃娃。
不只拒绝合照,走路时自然不与我并肩走,和我各牵一个孩子前后排列。她的话说得越来越少,即使说了,我的心分着,或是孩子插嘴,总是听不清楚彼此,多问两次,皆感到身心俱疲,唇焦舌敝。趁早起我仍熟睡的时候量体重,在密室更衣,切掉所有的夜灯,拉起不透光的窗帘,在黑洞里做爱。
我说过什么让她受伤吗?她变得畏缩,不只怕人,怕胖,也怕我,听我说起她,眼神滑开,尷尬地笑,流利搭着手边的小孩或家事脱身。
我常常一次说太多了,也说过太多了,是家人便无忧无虞,朝向她的言语几乎日常──嘴角有饭粒,牙缝有菜渣,衣角和袖摆沾到食物渍,头髮湿汗扁塌,浏海鬢角芜杂,身上蒸腾汗气。苦瓜发黄,竹笋太苦,水果乾涩,吃了一口鸡胸肉,无法遏制咽反射地乾呕了一声。
我不记得从哪一句话开始,逼退曾经外放的她,或许只要一句话就能摧毁她,即使突如其来的甜言蜜语也像讽刺。她被生活削得很薄,我们的爱情,已经输出婚纱照贴在墙上,大功告成。我们每天都变得更不一样,才过去几年,已是经轮迴遗忘的身世。
男人到中年充满瑕疵,我依然规律跑步,儘管拉长跑时,绕了多少圈还是跑回原来的体形,有时甚至越跑越胖,呼吸便让肚皮松弛。夜里连操场上都只剩我一个人,她陪孩子睡,不见任何萤火虫,路灯和车辆的光都来到我身上,我能将自己看得一清二楚,天空的云轮廓清晰,像有人端着强光直射。
回家之后,她躲进深沉的鼾声,她们三人一起开着冷气,裹着厚厚的棉被,像萤火虫之墓里清太与节子兄妹住的无光土穴,为什么美好的事物这么容易覆灭?电影里小妹妹节子的妈妈被炮弹烧死了,哥哥抓进土穴里的萤火虫隔天一早死光了,青春也是。
最近儿子长大上小学了,伶牙俐齿,开始什么都怪妈妈,上学迟到是妈妈的错,圈词作业写错要订正是妈妈害的,东西找不到是妈妈的问题,气势强大,一副大人样,指责连珠炮,毫无惭愧犹疑神色。女儿本来就凶悍性格,对妈妈爱得深,也任性到底。
妻子对这些总不反驳,也不承接,让所有话语落在身上,静静等候他们说完,彷佛正淋着一场雨,湿透的会乾。
我对妻子说,同事都是好人,不用太害怕,妳这样简直就跟萤火虫一模一样。
关于出外见人,我才该怕吧,这几年胖了几十公斤,再也不敢量体重,也不敢直视镜子。深夜跑完精神昂然,熬了更长的夜,皮肤比青春时长了更多痘子,不知是不是睡前灌了太多水,日日水肿,过午不消。紧张时习惯抠脸剥唇,挠刮手脚,脸上四肢随时挂着斑驳的血斑。
妻子说,不会的,你很好看,大家都会喜欢你。
不,我看妳拍我的相片,全部都好丑,妳都由下往上拍,或是从背后拍,痴肥又臃肿,我才知道我背影这么宽厚。
妻子说,才没有,我觉得很好看,我很喜欢。
我开始转而抱怨她让我吃得太多,毫无节制,变得肥胖,她说不会,她试着买过低卡低热量的食物,发现我忍耐着并不喜欢,看我吃得开心,她才开心。
她向来如此,说话癖性与我相反。在外面听到任何一点批评,我就惶恐到整身的血管都在跳动,转述给她听,她总替我愤怒驳斥,振振有词地提出反论。她比我明白──我心里禁止涉足的禁区比她更多,更难承受丝毫侵扰。
我理解了,是我独自一人卑怯地蹲进爱情的坟墓里,闪躲时光,想长得年轻,却活得苍老,爱得乏力。
关于萤火虫的习性,大多数飞在空中发光的萤火虫都是公的,蛰伏在地面的则是雌萤火虫,公萤火虫飞舞是为了求偶繁殖,吸引雌萤火虫的注意。雌虫其实会飞,也会发光,但不飞,因为负责产卵,增加了她的重量。
不同种萤火虫闪光的频率,只有同物种能够看到,还能藉着闪光彼此沟通,以固定的时间差回应,差零点一秒,就是陌生异种。
发光的萤火虫都是公的,导览员提到畏光避声,容易败亡的,或许也是指公萤火虫吧。
妻子说,她爸爸小时候曾为她抓过好多只萤火虫,放在昆虫饲养箱里,一整夜发亮,她兴奋地不睡,一直看,微缩的银河,爸爸半夜发现,生气地用毛毯盖着,她只好去睡,隔天醒来,全死了。她打开盖子,死去的虫极臭极臭。现在才知道原来里面全是公的。
我看见无声的黑夜里,我变成一只发光飞舞的萤火虫,从远方飞来,畏畏缩缩地颤抖飞行的路线,闪躲偽装的玻璃纸红光与交错喧嚣的足迹。她不是在躲藏,是长久驻守原地,等待着准备要躲藏的我,我们身上闪烁的发光器,为彼此传送氧化的密语。我停在她宽大的背上,周围是纯净的潺潺水流,潮湿的青苔,松软的泥土,合适的卵床与墓冢。炽烈的光线闪过空中,我们伏身在草丛里,终于完成任务,能够阅读彼此逐日黯灭的光影,生命的尽头就在眼前。
有人说,没自信的人,才会一直挑拣别人。
我对妻子说,好啦,想也知道妳不会去,我早就拒绝别人了。
妻子垂下嘴角,冷笑一声说,我才早知道你。
我想起陪孩子去看萤火虫那次,导览员说手搓热,萤火虫就会自动飞过来,我怎么搓,萤火虫都不飞来,跟在我身边的女儿不耐烦,看着飞离我们避得更远的萤火虫,开始发脾气。妻子搓着手,又乾又碎的皮茧摩擦声很明显,却已经招来又转手送给儿子好几只,女儿抛下我,跑到妻子身边。
我困惑地趋近问她怎么弄的,她随意搓搓手,靠近憩在草上的萤火虫,萤火虫便飘落在她手上。她再缓缓地握住我的手,萤火虫一动也不动,静静闪光,像快要睡着的眼眸,不愿意爬过来。但我讶异,她的手过了这么久,竟还是这么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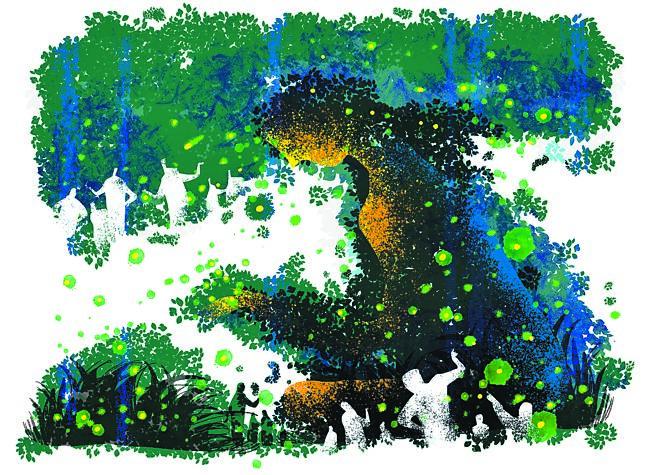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