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年代,一下笔就能把外景拉到杜拜或更远处的大有人在。对此,我只有望洋兴嘆的分。毕竟日月丽天,山河丽地,各有广阔的覆载,而我像百谷草木丽乎土,微幅摇摆,生活的田野由此展开。
*
清晓是一天的额角,光洁如银,舒展着弧形的寧静,直到鸟声将它啄破。社区里鸟儿生息眾多,除了寻常的麻雀、野鸽子,也有季节性的燕儿,以及肚腹圆润、纹路鲜明的翠鸟时来伫足。阳台早年给窃贼侵入过,所以安上了纱窗,早晚只有变幻不定的光能探进来。
记得是个假日的清早,突如其来的喧闹使我惊醒过来,四顾不见,我一下子无法明白那阵扑动跳盪是怎么回事。踱出阳台张望时,声音立刻安静了,像决心要留在暗处窥伺。〈聊斋〉里出现过许多神秘多情的小生物,鹦鹉、绿蜂、促织……,这会是哪一个呢?正好奇时,忽然一阵飞腾,眼前闪过一抹褐色的暗影,是麻雀!我有点失望,但翠鸟的机会本就不高。只见牠小小的身躯在我眼前迅疾地来回穿梭,顷刻间在空中画出了杂沓凌乱的虚线,奋力做困兽之斗。我连忙把窗大开,牠却二度沉默了。不知是出于气馁或警戒,牠蜷在墙角,久久没有动静。该不会负了伤?往常风雨的日子,家门口不时会出现坠地的雀鸟,奄奄一息,柔弱的抽搐着,当下心里掠过一丝恻然,却只能无知的束手旁观,次日天晴打扫便收拾了僵硬的鸟尸。此刻我感受到那一只困于狭仄空间的麻雀内心,正激盪着孤寂、慌张,生而为人,我要如何对另一个战栗的生命表示歉意?如果能有一枚所罗门王的指环,让牠明白,把窗打开,是鼓励而非恫吓。牠似乎秒懂了我的心思,陡然振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态笔直的穿窗而去。我愕然目送牠轻轻巧巧地降落在对面楼房的屋顶,临风顾盼,像颇为自得。我怀疑有那么一瞬,是否牠也正朝我转动着黑圆的眼珠?
经过一番仔细勘查,里外并没发现可出入的缺口。好天气的日子,我在阳台上洗濯衣物,不时仰起头来,欣赏天空下自由的飞鸟,这一次忍不住嘆息:世界上再怎么平凡无奇的翅膀,总不负于牠所遨游的美丽苍穹啊。
话说有翅膀的生命之中,蚊子是顶不受欢迎的。虽然亨利.梭罗曾经说,蚊子的飞行是人类无法想像的旅行,牠微弱的嘤鸣是荷马的安魂曲,是空中的奥德赛,吟唱流浪,其中具有某种宇宙的心怀。这无上的礼讚增添了华尔腾的风物之美,却无法为其他地区的蚊子加分。尤其亚热带的台湾,蚊子生命力强,灵性恐怕相对的低吧。
屋里的蚊子却不流浪。牠们在我脚边跳舞,睡梦中在我头顶打呼,逐鼻息而居(据说蚊类性好二氧化碳)。人们费尽心思来对付:薰牠电牠掌掴牠,渐渐发展出比较文明的精油和贴片,但总之不能使人完全心安。
饱受蚊害多年,某年夏天,我顿时领悟:有没有可能从「心」改起?我试着弯下腰,向蚊子精神喊话:「喂,别贪心,吻一下不嫌少,吻两下刚刚好。知足常乐才是王道。」为了展现人类恢宏的气度,顺便自我勉励一句:「堂堂血肉之躯,难道还喂不了几只蚊子?」有几回牠们竟然真的散了,我如愿获得了片刻安寧。就算照旧的闹,我也不再容易烦心。原来,该提升灵性的是我不是牠?
能够活到秋天的蚊子叫做「哀蚊」。蚊子是短命的生物,尖音家蚊的寿命只有七天。如果不是因为传染病,又何必赶尽杀绝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或许这就是一生倾慕东方的梭罗,看待华尔腾之蚊的宇宙心眼吧。而日本文化所咏嘆的哀蚊,让我们懂得怜惜那些活得渺小有限之物。生命儘管有凄凉的时刻,在余火尚未燃烧殆尽以前,何妨欣赏一下宝贵的微温犹存。
在我的芳邻中,对面住的是林太太,右边也是林太太。两位老人家年过八旬,却并非凄凉的哀蚊,不但不敏感自怜,而且还活得自尊。
认识两位林太太很久了。二十多年前,她们还是活力充沛的欧巴桑。「欧巴桑」是台湾国宝,有此认识的大概不多。这源于日本时代的称谓,现在已严重的污名化了。在讲究冻龄的潮流下,欧巴桑不善掩饰外貌风霜;在酷炫当道的都会中,她们被视作农村遗物。欧巴桑跃居年轻人口中的「马路三宝」─ 老人、女人、老女人,受到歧视和嘲笑。但她们多管閒事却不易受伤,热爱社交,是茧居族的暖系对照。一个没有欧巴桑的社区,该多寂寞!
对面林太太嗜好种花,对她来说这可不是什么消閒的玩意。她肩负着一个三口之家,从吃穿用度到维修扫除,全凭双手张罗,数十年如一。此外还热衷志工,图书馆、卫生所、社区小学都可看见她的身影。火红的摩托车一发动,她就化身城市游侠,来去如风。有人好心来劝,年事已高,何必如此忙碌?「不这样怎么行?」她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行动」,所以买花种花浇花,换盆除虫施肥,完全是不可省略的必要之事。
那年冬天林太太买回几株细瘦的山樱,春来便织出嫣红的窗景。草地上的繁星花开成一片,野百合伸出召唤夏日的号角,不久便交棒给玫瑰。花季绵延不断,引来隔壁林太太也伫足称赏。
隔壁林太太清閒人,每天一早到公园运动聊天。傍晚时分,偶然会听见她一个人在客厅开着卡拉OK唱歌。她三餐自炊自食,家人经常不见踪影。我喜欢趁散步时探头看她养在门口水箱里的乌龟,据说当初是年幼的孙女从夜市钓回来的玩物,二十年来长得硕大极了,非常安静,从早到晚在浅浅的水里划动着四肢,久久发出拨剌一声,又一声,我心头一动,彷佛听见长生的寂寥。
去年夏天丈夫罹癌,两位林太太都很关切。隔壁林太太常见外子在庭院扫除、剪草,义务做社区的工,她对着我嘆气:「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对面林太太在车库前叫住我,聊起来才知道,她长年守护的独子十九岁就罹癌,治疗的副作用影响很深,至今阴影还在,没有信心成家。「缺什么儘管告诉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林太太说。
近来我也开始走出家门去运动,向阳公园,多好听的名字!我一圈一圈的走着,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了这里的欧巴桑们:直肠子阿云、豁达的阿珍、诙谐阿凤,还有「狮子王」、憨憨的「第五」……。她们早就和我一起居住在这叫做「向阳里」的地方,直到今天才连繫起生活的田野。
愈到后来,我愈常回忆起从前居住的所在。大学毕业后,在台北市赁居。復兴南路三百四十巷,我私许为「桂花巷」,有户人家种的桂花特别香。凡有朋友来访,我就在电话里指路:「过辛亥路,沿復兴南路二段一直走,寻花香转进巷子第四家,就到了。」从没有人迷失过。
后来和朋友合力租下辛亥路边的公寓,三房一厅,虽然老旧,几个二十出头的女生却兴致勃勃的过起「拟家庭生活」。上班下班,沙发上堆着当日的报纸,厨房里传出快意翻炒的声响和饭香,歌唱的垃圾车来了,得有人迅速套上拖鞋衝下去。现世安稳,教人放心。然后房东太太携着女儿和外孙女从日本返来了。女儿刚离婚,精神状况欠佳,年迈的房东太太一手照料她们。台湾的冬天对日本小孩来说还是太热了,两岁的冈冢敦子常常脱个精光,在百废待兴的主卧室里大跳弹簧床,十分健壮活泼,陪玩的我们一下子就吃不消了。
敦子的母亲很阴沉,从不与我们打交道,也没见她开口说过话。才没多久,一天我们早起准备出门,发现门把上半夜给插上了剪刀,顿时人心惶惶,当晚先后火速迁出,我们的「家庭实验」就此草草收场。
多年以后偶然念及,很想知道,敦子是否平安长大了?过得还好吗?
大学期间自然是住宿的。宿舍的生态很丰富,各路传奇人物和流言在此翩翩起舞,后来成为补教女王的外文系美人儿就住在一楼。端午节会有人送来台湾各地的风味粽,背景迥异的室友们平时从家里带来分赠的小物无奇不有,妈妈手做的鸭赏、自家工厂生产的内裤都在其中。但也有人自外于一切交流。
我记得来自德国的安娜,她看来很严肃,略有几分抑郁。今天我当然懂了她孤身在外求学的焦虑,加上德国文化一板一眼的教养,使她成为眾人眼中一个古怪、神经质的家伙。她随时把门锁上,室友即使出去上个厕所也必须把钥匙随身带着。孤独的安娜,有那么一次来到我的房间,在书架前张望,忽然间伸手一指,说:「你喜欢他?」那是奥地利画家席勒(Egon Schiele 1890~1918)的册子。安娜告诉我:「在我们那里,很少人喜欢他,觉得脏。」然后我们一齐脱口而出:「但是我喜欢。」她腼腆的笑了。我但愿安娜对台湾生活的印象,至少有一点明亮的地方。
不能忘怀的是歷史系的林滴娟。大学头两年我们分配在同一间寝室,我还在高中生活的余韵中迴旋时,她已游入了知识的蓝海。她很早就立志读史,除了系上的功课,还勤跑民间私塾。第一年的校庆来临,女生宿舍对外开放,一束红玫瑰递进了419室,我们几个新鲜人见证她迎接人生初次的爱情。当年在卧虎藏龙的学府里,她是很惹眼的一颗星。
她陨落于一九九八年,得年三十二。身为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的林滴娟,偕男友赴中国东北洽商时遭绑架杀害。整整一星期,她都是头条。我守在晚间电视新闻前,目击她躺在玻璃罩的棺木里,着紫色荷叶边无袖洋装,被鲜花簇拥着,像一个新娘。也许她早就准备做民主的新娘,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林滴娟加入甫成立的台大浊水溪社,不久和男友分手,一步步走向从政之路。
我曾梦见她,身穿一袭碎花裙,用甜美如昔的嗓音唱着〈爱的真谛〉,醒来后怅惘不已。滴娟一直是很热情的人,我相信她已得到安息。
*
到眼前这年代,多数人走得更远了,而我则不。身体的限制将我留在家乡,生活的田野就在脚边。而我所曾经居住的地方,遇见的人,终将成为传说中的息壤,我长大,它也跟着长,直到我们合而为一,不负生长于斯、这天清海阔的岛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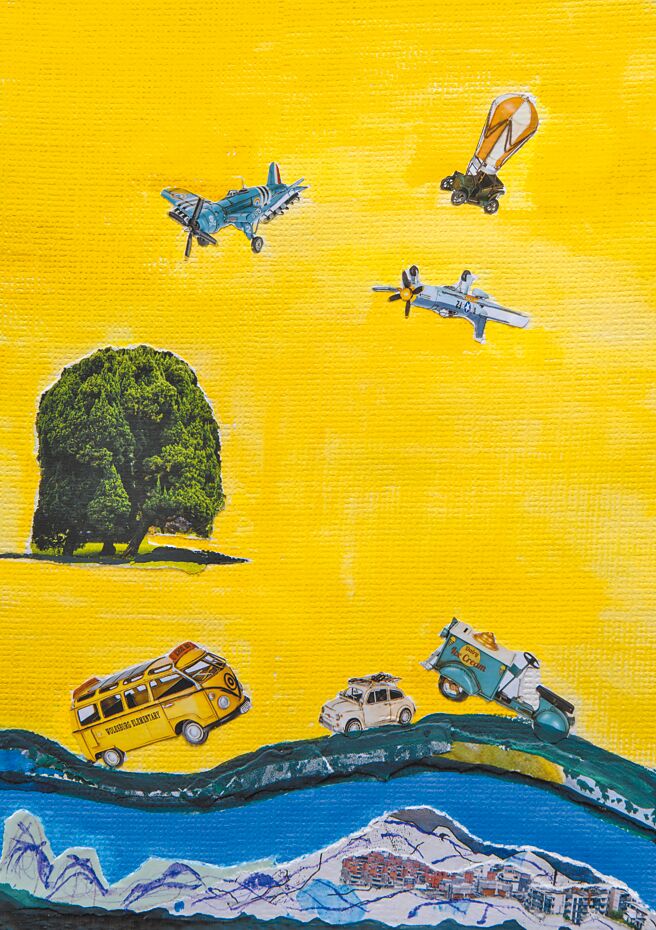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