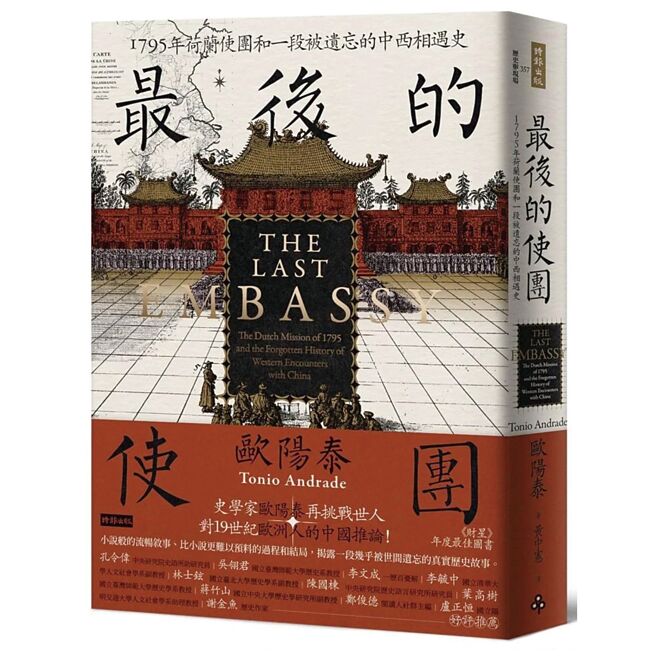
就这点来说,他并非独一无二的荷兰人。荷兰人深深打入东亚世界,一般来讲照东亚规矩行事。但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十七世纪初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刚成立不久时,该公司发炮闯入中国海域,要求给予贸易特权,未能如愿时即出手攻击。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反击,在中国沿岸和沿海的一连串交手中打败该公司。荷兰人得到教训,从此比较听话,得到与中国人通商的回报,中国人的商贸活动进到荷兰人在亚洲的诸多据点。明灭清兴(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荷兰人是最早派出使团并得到清廷接纳的西方人,而且荷兰使者未对叩头礼表示异议。西元一七○○年之前另有两个荷兰使团得到清廷接纳,每个使团都按清廷规矩行事。荷兰东印度公司靠着与中国贸易而财源滚滚。
荷兰人在日本也学乖。在那里,该公司碰上很难对付的德川将军。该公司最初也咄咄逼人,最后不得不听话,每年遣使向德川将军叩头,一如日本诸侯向将军叩头。一如在中国,守规矩就有好处。荷兰人是唯一获准在日本通商的西方人,而日本是获利甚大的市场。
与此同时,荷兰人在其殖民地首府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建立了自己在亚洲的朝廷。他们接待来自亚洲各地和远从非洲过来的代表团,採用东南亚、东亚的外交习惯和器物,例如伞和大象游行。诚如史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e)所指出的,「巴达维亚政府找到与亚洲诸统治者相处之道,懂得照当时其所注意到的亚洲盛行的外交礼仪和规矩行事。开拓殖民地的荷兰人不得不发展出『东方』仪礼,以配合既有的外交互动规则。」
荷兰人藉此理解包乐史所谓的「东方外交」,而且大体上接受这样的外交。他们认识到在东亚,国际关系受到诸多不同理想规范。关系尊卑很明确;遣使的用意主要在于祝贺或庆祝,而非谈判;互动通常遵照仪礼,许多仪礼以中国古老传统为本。
迁就非西发利亚式外交的西方人,不只荷兰人。「新外交史」的学者已指出,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外交体制,远比长年以来所认为的懂得变通而不拘形式,表示欧洲人常常使出多种外交手段。就连英国人都对东亚外交礼节有基本的掌握。
无论如何,得胜一行人接受清朝礼仪,对于朝廷互动规矩应付自如。他们也精于记录下自己的经歷。他们翔实的文字纪录,加上其他多种丰富的资料,为瞭解十八世纪中国开了独一无二的视角。事实上,这些资料叙述极生动,使我下笔时能如身临其境一般,而且我採取叙事性微歷史做法。微歷史(microhistory)通常着墨于次要事件或「小人物」,也就是通常未见诸歷史记载的人物。本书的主要人物,系一些有钱且得天独厚的人─欧洲人、汉人、满人─而这次荷兰遣使访华并非次要事件。但大故事里的人间小戏码吸引我:恐惧、忧虑、沮丧、幽默、小小的龃龉。此行的年轻团员在北京北海溜冰时爱用欧洲冰鞋甚于满人冰鞋一事,或他们怕走过没有栏杆的桥一事,对中西关系史来说,或许无关宏旨,但这些小事使歷史更为生动活泼,有助于我们想像在十八世纪中国居住、旅行的情景。(四之四;摘自《最后的使团》)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