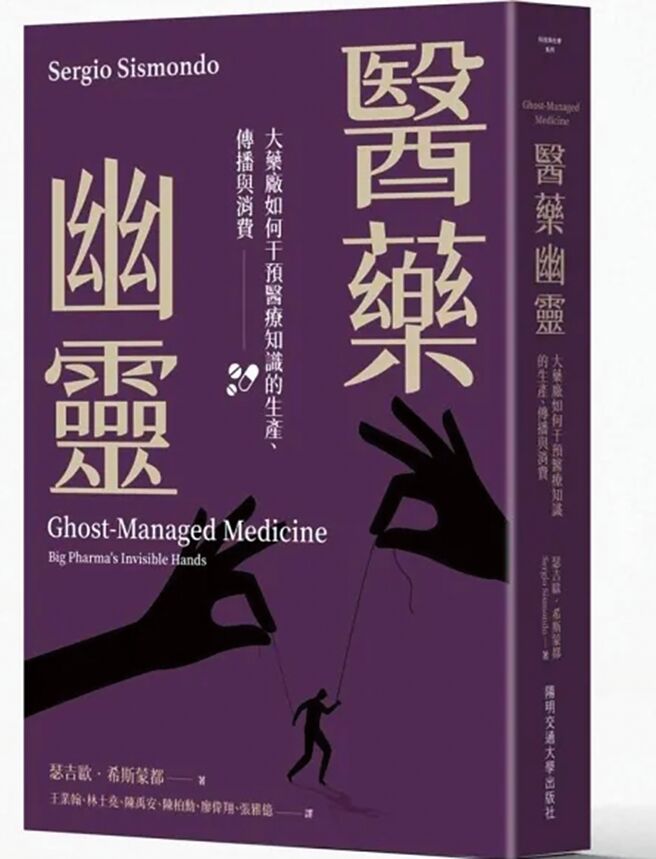
在各种形式的医学传播周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服务产业。行销人员宣扬他们有能力「透过教育推销」,并声称继续医学教育能够「客制化以符合药厂行销者的需求」。身为药厂的代理人,医学教育与传播公司(medic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mpanies,简称MECC)开发课程、规划会议与专题讨论、实施调查,并且撰写论文与研究。接着这一切被交托到教育者、研究者与医师手中,而他们会有效地利用这些材料。这些公司将故事喂给报纸和医学杂志的撰稿记者,提供他们技术细节、期刊论文与需要联络的专家姓名,就连叙事结构也替他们想好了。他们甚至还提供短片给电视网,接着电视就会播报相关的最新进展。
现在轮到地面部队:药厂业务代表。这些男男女女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为了要增加药品销量。而要增加销量,就意味着得说服医师「改变他们开处方的模式」。这句话的各种变换说法在制药产业的圈子内一再出现。为了说服医师改变开处方的模式,业务代表採取的做法是巧妙地围攻他们,有效地耗尽他们的能动性(独立行动的能力)。业务代表来到医师诊间时,就已经知道他们的目标对象会开什么药、对方的自我评价如何,以及一大堆可能利于建立关系的琐碎资讯。他们也备妥了为大部分情况所拟定的脚本,因而对医师的迴避举动早有准备。如此一来,就算医师认为自己是透过互动才独立做出决定,但其实业务代表早占据了有利位置,能将那些决定导向于开立正在讨论中的新药物处方。医师觉得他们掌握了局势和自身行动的同时,业务代表正悄悄地「改变开处方的模式」。这些业务代表善用了药厂委托与形塑的科学研究。医学科学贩卖药物的方式,就是允许医师做出理由充分的决定。
病友权益倡议人士与组织在药物的幽灵行销中是更重要的环节。美国有三分之二的病友权益倡议组织接受产业资助,而这群团体中有45%的资金是来自制药、医材以及生技公司。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面前做简报或参与内部讨论的病友权益倡议组织中,约有93%接受药厂资助。其他的高所得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例如英国。
在极端的案例中,病友权益倡议组织是属于制药产业的产物。他们完全由一或多家公司资助,由专业人士担任工作人员,并在事后找病友来担任成员。他们就像其他受资助的病友权益倡议组织那样,担任说客并进行公关工作,包括推广药物与疾病,以及为药厂辩护以对抗坏名声。他们是药厂的赛莲海妖(sirens),热情歌颂着更好的未来里会有更好的药物。至于药厂的另一种幽灵「无形之手」,则忙于操纵其他行动者,努力不懈地为药厂掩饰动机与利益。
总的来说,药厂仰赖的做法就是系统性地推动科学知识的流动与其所导致的医疗行为,透过隐微及幽灵般的行事作风,会使这套具影响力的系统更为有效。
由于我将重点放在医学内与紧邻医学周遭的幽灵行销上,因此将不会在本书中讨论更显而易见的行销种类。举例来说,在二○一六年的美国(对药物广告态度最开放的大国),制药产业整体购买了超过三十亿美元的电视广告,并花了几乎同样多的钱在报章杂志和其他媒体的广告上。在那之中,有三亿美元流向医学期刊的广告。
或许是因为庞大的广告支出,导致药厂能对电视网及其他媒体(包括医学期刊)发挥杠杆作用,进而扩大制药产业的影响力。然而,为了限定讨论范围,在此我不会对药厂的杠杆作用多加探讨。
药厂有许多他们能直接掌控的代理人,例如为达到特定目的或创造特定产品而雇用的公司、机构、事务所和谘询顾问。透过外包给这些代理人,药厂得以利用外部专业与资源,并拓展其影响范围。我在本书中描述的代理人(包括药厂花最多钱在上头的那些)受雇是为了要制造或传布资讯,使市场的其他要素(包括监管单位、医师、病患)接受这些资讯。药厂及其代理人透过形塑对方所知道与相信的事,从而影响那些市场要素。监管单位、医师和病患接着以看似理性、明显或容易的方式做出行动。若是药厂成功达到目的,他们就能局限住目标对象的能动性,就类似西洋棋老手在面对较青涩的新手时,能隔着桌子压制对方的能动性一样。三之三摘自《医药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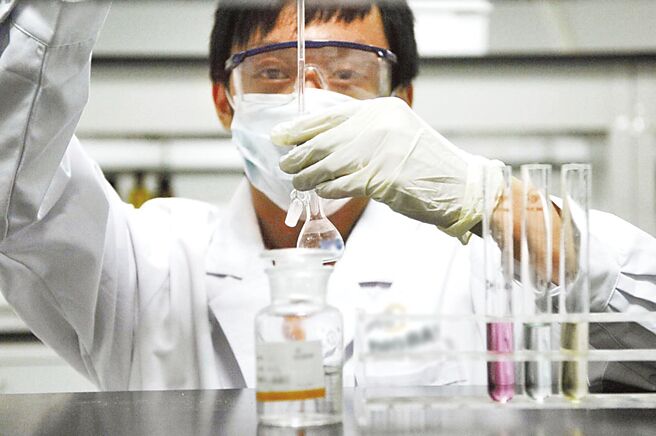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