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成功,首先是他的人品,他恪守中国儒家文化,崇孝悌,讲义气,重人情,疏钱财……以此博得别人的尊敬。
张大千是非常孝顺自己的母亲的,从8岁开始,每晚临睡时,必跪在母亲床前,给母亲请安洗脚,同时汇报一天的功课,十几年如一日,直到离开内江,外出游学。他搬往网狮园时,已经非常有名气了,但只要回到老家,仍坚持旧习,不忘记给母亲洗脚。据老辈回忆,曾太夫人曾摸着他的头说:「爰儿啊,你今年34岁了,今后洗脚的事就交给丫鬟们吧。」
大千回答:「能给娘洗脚是儿的福气,只要儿在娘的身边一天,这份孝心是一定要尽的!」
张大千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外,早期靠善子跟他建立社会关系,善子早年在日本留学,跟随孙中山,认识许多上层精英,如张群、于右任等,日后都成了张大千的挚友,尤其是张群,他俩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终老;经济上靠的是三哥丽诚,他是个民族工业家,是长江福星轮船公司和贵州卷烟厂的创办人,是张家经济的掌门人;四哥文修,写得一手好字,诗词也做得好,对大千在文学方面的长进帮助很大。
张大千是一个尊崇「孝悌」的人,不管他流落到哪里,一直把几位兄长的照片带在身边,今天挂在台北「摩耶精舍」的画室里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张家的三妳(mi)。──张大千的三嫂罗正明,比大千长15岁,在张家发迹前,嫁给张丽诚做童养媳。在张家贫寒的岁月里,是他背着年幼的张大千,怄着腰,在别家收过的红苕地里,翻找遗留的小红苕,嚼碎喂养,以致大千晚年,每每向人提及此时,就哽咽不语。
当台海两岸政治略有松动,他就托朋友一位年轻朋友回大陆探望三嫂,并一再嘱托,要代他行三跪之礼,说罢,拜倒地要向比他年轻几十岁的朋友磕头,请他把大礼带回去转送三嫂,唬得那位朋友连连惊呼:「老太爷,我不敢当,我回去送你一个大礼就是了。」那天他送那位朋友出门,还不住叮嘱:「一定要将你代我向我三嫂磕头的照片带回来!」
大陆的文革动乱刚平息,张大千就写信给在上海的侄女张嘉德,他是张善子的么女,笔者当年亲见此信,是写在一幅红梅喜鹊图上的(此图今年在苏富比拍卖),二尺见方,信的大意是:大陆局势趋向平稳,外出探亲也已宽松,你将此信出示当局,可获赴港签证,抵港后我会托人办理余事云云。
不久张嘉德带领女儿端端去了香港。当时台湾政局尚未开禁,台方怀疑张氏母女是大陆政府派出去统战的,再加上上海文史馆开统战会议时,陈巨来信口说,张大千已有家属放出去搞统战了。
此言很快传入台方,致使张氏母女滞留在香港徐伯郊家中数月。徐伯郊是着名鉴定家徐森玉的儿子,他受张大千委托,为张嘉德母女入台,尽力奔波,但毫无成效,最后不得不由张大千亲自带了两幅画,拜访蒋经国,说:「我的成就,全赖先仲兄提携,嘉德是先仲兄的么女,先仲兄逝世时,她只有14岁,为报先仲兄之恩,我寧可不担保自己的亲生子女,但一定要将嘉德母女担保出来,请您高援贵手。」
在张大千的力求下,蒋经国特批张嘉德母女入境,同时被批准的,还有何应钦的一位亲属。据张大千的十一女张心庆说,他申请赴台曾被拒,官方的理由是你父亲说,只担保侄女张嘉德,自己子女一个也不保,并留有字据。
张大千在大陆时,张家几房弟兄不分家,子侄几十人生活在一起,俨然是一个鼎食鸣钟之家。张家的称呼也特别有意思,子侄们一律叫善子为「阿爸」,(善子没有生儿子,四哥文修将彼得;大千将葆罗兼祧给二房,不幸彼得在阿根廷得白喉早夭,葆罗有幸跟随大千,从巴西到美国,又到台湾,前几年在美国逝世)。张家的子侄,一律喊善子为「阿爸」,喊大千则为「爸爸」,(因为大千在老辈中排行第八,有谐音「八八」的含义)。
张善子为人不苟言笑,说话处事非常严肃,家里人都怕他,只要他在家,孩子们都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在重庆时,有一次善子出门,孩子们看见阿爸走了,一下子开了禁,带上脸谱,挂起鬍子,敲锣击鼓,把画案当作戏台,上下蹦跳,演起京戏来,不料善子回家取东西,看见画室变成戏台,笔墨纸砚弄得一团糟,气得他鬍鬚倒竖,一声虎啸(张善子号「虎痴」),下令孩子们全部跪下,手执戒尺,打了个满堂红。如今已经80多岁的当事人,回忆往事,都禁不住开怀大笑,都说阿爸严厉,会打人,而爸爸的脾气好,我们有错他会开导,讲道理,不打人。
张大千的成功是以儒家的孝悌为前题的。
近代画坛,派别纷杂,尤其两岸分隔,毁誉各说,然而被眾口一致讚誉的,惟有张大千一人而已,真是「五百年来第一人也」,此话不虚。
(作者为旅澳华人作家)
【未完待续,〈你所不知道的张大千〉每周六连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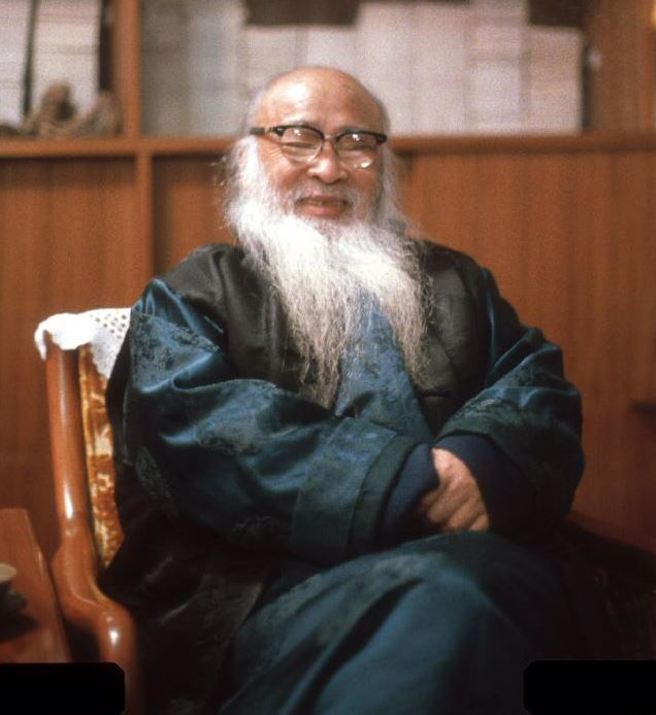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