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6日,我在乌坵看《我的家乡在乌坵》,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经验。
难得之处在于,乌坵很难去得了。乌坵乡有大坵、小坵二岛二村,设籍人口600多人(长住居民不到30位),面积仅约1.2平方公里,位于马祖与金门的中心点,西南距金门72浬,东距台中约80浬,对外定期交通只靠15天一航次的军方船只由台湾的台中港往返,而且到现在仍是军事管制区,非当地居民须经申请许可方准登岛。因此即使乌坵乡划归金门县代管,绝大多数的金门人也都没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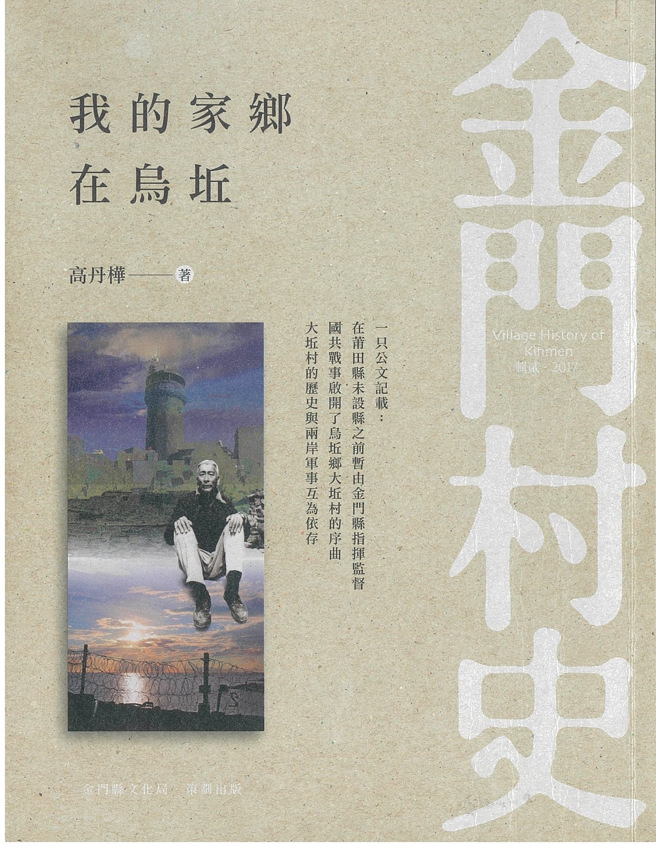
我2018年2月起曾长住金门,读了金门村史《我的家乡在乌坵》(高丹华女士着)之后,就一直期待着要带这本书去现场对照着看,等了四年多,终于如愿以偿。
6月6日清晨七点,在金门县文化局文资科杨至臻先生的协助下,我与金门大学建筑系曾逸仁教授研究团队,到金门水头码头和交通部航港局代表会合,一行十余人搭乘专船于八点出发,顶着大浪前进,同船者有一半以上晕船不适,到了下午二点多,才航抵大坵岛附近海面。由于潮汐的缘故,又赖军方橡皮艇分三次接驳,这才顺利登岛会勘乌坵灯塔附属建筑物,完成其存废与再利用的评估工作。
由于此行无法过夜,船长说下午四点就得回航,要争取晚上十一点之前回到金门,所以别说小坵岛上不去,就连大坵岛也没时间走一圈。我虽然不无遗憾,但能亲自登上清同治十三年(1874)由英国建筑师汉迪森(D.M.Henderson)设计监造完成、2018年指定为国定古蹟的乌坵灯塔,并到塔旁挪威籍塔守雅格森(H.J.Jacobsen,?-1899)的坟墓前凭吊,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何况我还去了大坵妈祖庙重建现场,并在观音庙见到暂时寄放的湄洲岛妈祖古神像。

就在乌坵屿灯塔上,我取出随身携带的《我的家乡在乌坵》,翻看书中第43页的「乌坵岛」(含乌坵灯塔、大坵村及码头)手绘彩图,以及第二章「珍贵的岛屿文化:人文资产与冷战遗址」的几张老照片,对照着眼前所见景象,果然见识到高丹华笔下「被遗忘的边陲」的荒凉美景。我看着对面的小坵岛,心想1998年乌坵要是真的成为台电公司核废料的储存地,那么现有的传统渔场、海上紫菜田就将永远消失了。

我知道我在乌坵看《我的家乡在乌坵》,书中所载许多人事物必然早已消失,例如往昔横行岛上的海盗、1949年的杀戮战争、1950年游击队司令官吴建自制的钞票(他在一张张草纸上签名盖章当作国币使用,向百姓强行购物),1960年代每张票价12元新台币的军中公共茶室,以及高丹华小时候随手就挖得到的紫水晶……,即使我此刻身在乌坵也是看不到的了。然而,现在看不到并不表示它们过去不存在,而这也正是金门村史书写的重要意义。
以前我看过公共电视台2003年拍摄的乌坵纪录片,片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是高丹华介绍说乌坵岛都是花岗岩,早期没有树,很多树都是阿兵哥画在房子上和大石头上的。可惜我们这次停留时间太短,没能去寻找刻画在花岗石上的大树,也无法去参观居民石头屋里的防空洞。

返航途中,曾逸仁教授说以后应该找几个朋友包船过来,申请多住几天,以便深入认识乌坵。我建议最好选在乌坵紫菜採收的季节,那时返乡的乌坵人多,说不定可以打听到更多关于乌坵的动人故事。此外,乌坵旧属福建莆田,老一辈的乌坵人乃台湾罕见使用兴化话的族群,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欣闻出身看守乌坵灯塔家族的高丹华又有新书《那些年我们在乌坵的日子》即将问世,我衷心期待不久的将来,能与朋友再访乌坵,住在乌坵,让我们一起在乌坵看《那些年我们在乌坵的日子》,这又会是多么令人喜悦的难得经验啊。
(陈益源/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