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父亲要我把家里不知又搁又丢了多少次,但随着屡次搬家迁徙仍不离不弃的那本《三国演义》给找出来。我想父亲最近沉迷练习书法,大概想是对章回里面的定场诗有兴趣,想练习一下吧,便在洗衣房里,满满老书的书柜中掏出了这本封面红皮依旧坚固,但是烫金字样已经完全剥落的小说。
父亲用放大镜看没几行字后,就兴致全消地将书丢到一边,并嘟囔着以为这本书是讲什么人生处事的权谋和哲理,原来只不过是本故事书。看着这本封面只剩下《三国演义》四字凹痕的「故事书」,童年的回忆便涌上心头。
小学时,书还是那本书,但感觉比现在厚重庞大得多,当我好奇地捧起这本书时,旁边的大人都说我那是文言文,绝对看不懂。要看三国故事就去看漫画、卡通,或是汉声的《中国童话》系列等故事书。反正三国故事从古到今都传唱不已,各种书籍和媒体、甚至天马行空的奇想,总数可说是汗牛充栋,何必拘泥那一本距离现代好几百年的老书呢?
这本红皮老书一直在祖父拼凑组装的书架上,每当我跑进祖父的书房,都会情不自禁看向那本「潘朵拉之盒」,直到小学三四年级时,我两三下跳上祖父床头,趴着地板将那本有点重量的书打开。
从小看书有个习惯:不从第一页开始翻,而是从自己觉得有兴趣的部分开始看,再衍生到各个章节,慢慢将全书看完:我最初看的桥段就是「长阪坡」:先是赵云带着阿斗在曹军阵营中如入无人之境,杀得在高处观战的曹操讚嘆不已;再是张飞喝断长阪桥,惊得曹操大军无人敢越雷池一步;最后曹操虽然识破了张飞的虚张声势,但诸葛亮和关羽带着不愿投曹的荆州水军前来相救,又让曹操直呼中计草草收兵。虽然那篇回目是「刘豫州败走汉津口」:刘备带着不愿投降曹操的平民百姓向南撤退,但还是遭到曹操精锐的追击,差点走投无路。但从头到尾的铺陈就像是刘皇叔带着一眾英雄豪杰,在诸葛亮的运筹帷幄下再一次挫败了曹操,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然后就是接下赤壁之战的高潮戏。
虽然如大人所言的,书中的文言文看得是懵懵懂懂,但看不懂的部分我可以背,多看几次把情节背起来后,也就慢慢以自己的方式把看似生涩的遣词用字理解下来,正确性倒也是有十之七八。藉此看懂了更多精彩的故事:小霸王孙策大战太史慈收服江东、被设定为奸雄的曹操竟得天时相助,一夜之间在渭水畔建起冰城,让不久前还连战连胜,搞得曹操割鬚弃袍丑态大出的马超阵脚大乱、还有那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南蛮王孟获,是如何在诸葛亮手中各种洋相毕露,七擒七纵后不服也得服…
自此之后,这本应该是在祖父书架上的书就搬到我的枕边「安家落户」。有次甚至突发奇想,拿着这本三国演义当作枕头入睡,想体验一下以书当枕究竟是怎样的感觉。
大陆中央电视台《三国演义》在台上映,一时引为风潮,由于剧中的情节对白几乎都是照抄原版《三国演义》,记得关羽斩顏良时,当曹操和关羽在阵前指着敌军阵势讨论,电视前的我先学着曹操的语调,说着「河北兵马如此雄壮」,然后立刻下意识地接着剧中关羽的回答「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当关羽策马衝入阵中,斩顏良首级而还后,我似乎也和剧中的关公一样收穫了家人惊奇钦佩的眼神。
此后「我会背三国演义」的话题就成了亲戚间的谈资,惊奇于我真的把那本满满之乎者也的书彻底吞下去了。
这件事的影响力甚至直到我上大学,当一堂课上教授边绕着教室,边问学生《三国演义》最大的转折点是哪里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了「走麦城」,不大不小的声音让走到身旁的教授听个正着,立刻问我理由,我只说了句「此后英雄开始退场」,教授显然满意我的回答,顺着我的答案继续他的讲课。
负笈远行的我,早已将当年那本捧在掌心视若珍宝的老书当作祖父遗物之一,随手和家中的各类书籍摆在一起,只剩下「喔,家里有这么一本书啊!」的印象,直到父亲要我把它从书堆中再掏出来时,除了红皮仍旧坚固外,内页似乎比记忆更泛黄了些,在手中也没那么庞大沉重,自己和书之间只剩下那段趴在地板上,吃着零食看着书,无忧无虑看着过去英雄们风采的记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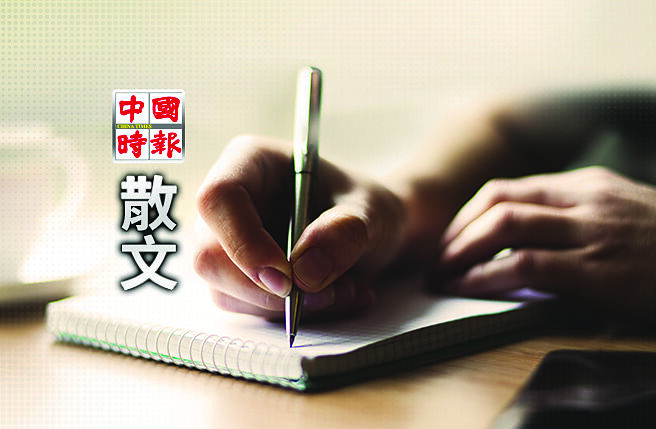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