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沦陷的消息是经由什么样的媒体传播到江南呢?北京失陷后,理所当然邸报的发行也断绝了。江南的人们取得北京消息,可能是有几项来源。举其中一例来看,如冯梦龙《甲申纪事》收录的〈嵩江(松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中列举其消息根据,「汝成之降贼,与贼之爱汝成也,一见于杨御蕃之塘报,一见于逆孽杨时亮之办单,一见于徐敬时之口述,一见于《国难纪闻》」。以下将分作:北京的消息首先传抵江南的过程即第一次传播,以及在江南广传到各地士民的过程即第二次传播,藉此检讨各种传播消息的手段。
在第一次传播的过程中,最为详细且重要的消息来源,即是来自北京的避难者的体验谈。北来的避难者所带来的消息,往往与提供消息者的姓名一同广布流传。从北京来的避难者最早到达江南的时间,可能是在四月初。苏州生员袁良弼的〈公讨降贼偽官项煜宋学显钱位坤汤有庆檄〉(《甲申纪事》所收),可以认为是撰写于五月十日的袭击事件之前,文云:「初逆贼魏学濂家人自北逃归,暂止西郊,已凿凿言诸贼从逆丑状,即应声罪公讨,然弼等犹谓,乱臣贼子之名,岂可轻以加人。迨迟之浃月,而南还者接踵,不但口诛无异,抑且笔记昭然。」由此来看,最初对苏州人士提到从逆诸臣消息的,是四月初左右抵达苏州的魏学濂的奴仆(前述)。其后,从北京逃亡到江南的人数增加,他们所提供的体验谈也逐渐广布,而关于其广布过程中所出版的各种刊物之详情将留待下节讨论,在此先简单地就相当初期的消息提供者进行探讨。
关于四月十七日到达南京的魏照乘,已如前述,他是在可谓当时江南情报中心的苏州的消息提供者,并且在往后的消息传布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冯梦龙在《甲申纪事》的序文中,统整他获得的北京消息的出处,列举如下:「甲申燕都之变,道路既壅,风闻溢言,未可尽信,候选进士沂水彭遇颷于四月一日,候选经歷慈溪冯日新于十二日,东海布衣盛国芳于十九日,后逃回,各有述略,不无同异。武进士张魁十六日出京,有北来公道单,叙忠逆近实而未及纪事,吾乡有贾人于五月望日出城,则李贼已遯,而燕京化为胡国,所述甚悉。」这里提到的盛国芳这号人物,在前述于松江府的讨伐杨汝成的檄文,以及苏州府的讨伐项煜的檄文,都是把他们作为实际可见的在北京的投降者之丑态的证人而引出他们的名字,如此一来不难想像这些檄文的起草者,是从北来避难者收集第一手消息的状况。
《丹午笔记》所收王心一等人的〈讨时敏檄〉中,作为见证时敏投降的证人,列出的有魏学濂的家人、吴尔壎的家人、武进士王三锡、京商周云章等名字,总的来说,北京消息的提供者,与其说是高级官员,不如说比较多的是奴仆或商人等庶民,或未任官的士大夫等。原因在于,他们在尚未被李自成军召唤之前就逃走了,同时也反映当时江南的氛围是对于高级官员的逃难者,他们未能殉国而遭到责难猜疑的眼光。
作为将北京消息传到江南的第一次传播的媒体,要举出的第二种是军事消息传达的手段。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到五月邸报断绝的期间里,塘报成为传播北京消息的重要手段。朱传誉提到明末几则塘报的例子,并指出:「一般来说,崇祯时塘报大多是军方直接派人探报,……。北都沦陷以后,所谓『塘报』,都是得自民间。」关于当时把北京沦陷的状况传播到江南的塘报,在此可举几则具体的例子。上海图书馆编《甲申纪事》附载的〈张士仪禀报思宗缢死及京师情形〉,是由副总兵张士仪以四月二日逃离北京的工匠们其口述为基础而作成的简单报告,于四月二十二日以后发布,文末是以「大变是的。日已久矣,四方必闻,恐有不肖之念者、乘之而起,则削平为难。莫若急求亲王绍统,颁诏发丧,则海内復知有君,不敢乱动矣」的建议作为结语。《爝火录》收录的〈陈方策塘报〉,与其说是传播消息,不如说是指出李自成军的弱点,并且呼吁反攻的文章。冯梦龙《甲申纪事》也是,不仅有陈方策塘报的节略内容,还收录陈方策寄给史可法的书简,根据文中注记提到陈方策是福建省莆田出身的监生。前述松江府讨伐杨汝成的檄文中,提到「杨御蕃的塘报」,就管见所及的范围内并未能找到该篇原文,不过,在上海人叶梦珠《阅世编》卷十载有提及山东总兵杨御蕃的塘报的记事,根据这篇记事,「甲申之变,相传开彰义门献城者,曹化淳也。据山东总兵杨御蕃塘报,又云是兵部尚书张缙彦」。就塘报其文书属性而言,虽然是以特定官员而非不特定多数的人们为对象,但是可能也有相当多人能知道这些塘报的内容。
第三种传达北京消息的资料源头,是史料提到的所谓「北来单」或「公道单」。前引冯梦龙《甲申纪事》的序文载有:「武进士张魁十六日出京,有北来公道单,叙忠逆近实,而未及纪事。」冯梦龙在《绅志略》报导在京各官的动向时,也时常以「北来单」作为根据。虽然其形式与内容不明,但是从《绅志略》的记事来想像的话,应是在姓名之下注记「死难」、「以老释归」等内容。从程源《孤臣纪哭》四月十七日的记事中,提到「遇京城逃人至,出一单云,吏政府一本,为考选事,谕新考选诸臣于初六日见朝,所载七十余人」来看,这些「单」应是李自成军为了联络和统制官员们而发出。对于相当关心在京官员们之动静的江南民眾,这些「单」由于正是出自李自成军之手,因此具有使投降的官员们无法辩解的直接证据的效果。
从北京返回的人所带的消息以及他们携回的「公道单」或是塘报等所载消息,除了藉由口传舆论散布以外,还以印刷品的形式广泛流布于整体江南社会。关于这样的第二次传播手段,最后进行简单地探讨。
根据姚廷遴的《歷年记》,他是经由「小报」取得北京噩耗的消息。关于民间新闻「小报」,歷来在中国新闻史研究即已论及。不过,关于小报的史料多属片断,特别是能显示明末清初小报内容的史料又是极少。在这一点上,《歷年记》提供的例子可谓贵重。姚廷遴的友人所持的小报,将皇帝自杀的日子误记为四月二十五日,虽然完全是杜撰的内容,但是在重大事件发生之际,恐怕就是这类被刊行的印刷品在民间社会广泛流传。《歷年记》接着提到「不一日大报到」,这「大报」是指什么呢?大报与小报的区别,与其说是反映纸张大小或记事长短,不如说可能是指官方发行还是私人发行的区别。例如,依据《启祯记闻录》提到,同年五月「南直巡抚郑(瑄),有告示刊印遍布。大意云,先帝不幸受害,南都大臣魏国公徐、兵部大堂史等,拥戴神宗次子首藩福王,于五月初三日登监国之位。……眾宜安戢静听,毋生疑惧。此示。余十三日于承天寺前见之」。当然,《歷年记》所言「大报」,不一定与这则告示是相同之物,但是被刊行且广布的这种告示一类或许即称为「大报」。(三之二:摘自时报文化《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更多精彩内容请免费下载《翻爆》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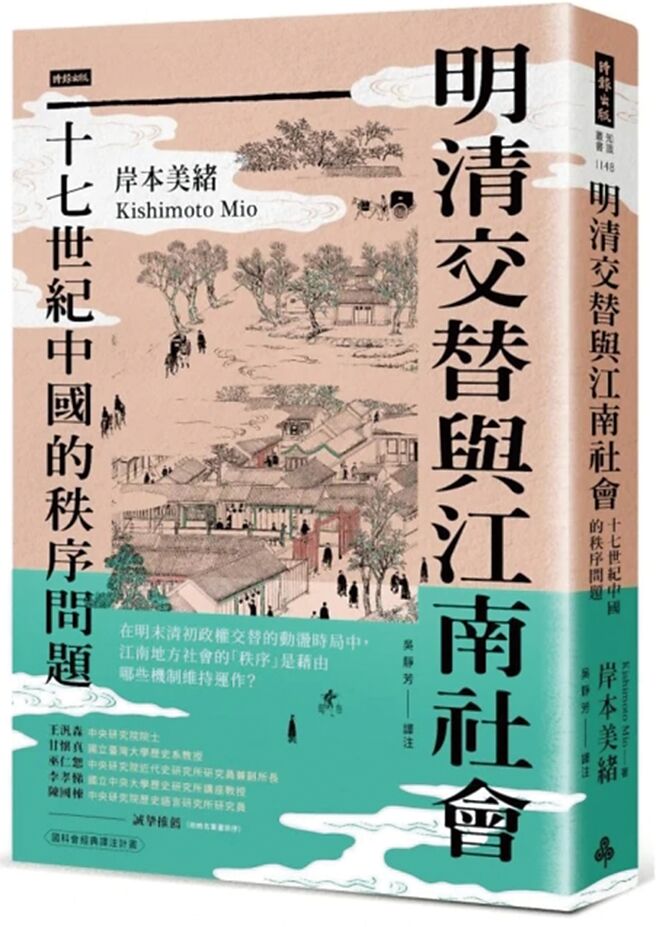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