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会」是一个具有各种含意又笼统的词汇,其实在所谓「地域社会论」问世之前,明清史学界已经着眼于「地域」,积极地进行多样的研究。第一,是从如此广大且不能一概而论的中国此一观点出发,对于各自不同的地域,例如江南、华北、福建等虽然广幅互异,但仍从产业、文化等方面选取出具备固有特色的地域。第二,比起各个地域的不同特色,毋寧说更着眼于以体系的统合性与自立性来划分地域的方法。像是以河川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体系的观点,将中国分为八或九个大地域的施坚雅提出的宏观区域理论即为一例。不仅有将中国划分几个区域的观点,相反地也有像是「朝贡贸易体系」,提出超越中国范畴的广域式体系的构想。这里的第一、第二所指的「地域」,与人文地理学中「同质地域」、「机能地域」的概念各自吻合。第三,与地理的、空间的大小无关,还有从社会阶层这一观点来关注当地社会的研究动向。日本战后的中国史学界,研究者所关注的并非宫廷、中央政府层级的政治史,而多是在处理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阶级对立的社会经济史;在欧美史学界也是,提出对比于静态的、理念的国家秩序图像,从充满纷争的地方社会实况更能发现动态的「歷史」的主张,这自一九七○年代以降益加显着。
从如上情况来看,对「地域社会」的关注并不能说是「新」的视角。我的意图也不在于特别标榜其新颖性。虽然如此,二十世纪八○年代以后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中,还可不可以发现与以往不同的共同特色?这些特色是不是值得注目?这才是我几次提及「地域社会论」的动机。
那么,上述观点的共通特色为何?请容我引用山田贤出色的赅括,他曾将总称为「地域社会论」的研究所蕴含的思潮归纳如下,并自谦是「随意的」总结。
「地域社会」、「地方社会」、「在地社会」等,是个人与个人相遇,取得社会关系连结,并且那样的社会关系连结在互相重复来往接触下形成社会关系网络的「场域」。在这些「场」里,有着让社会逐渐凝聚为一个整体组织的磁力(或是对于具备对抗动机的反统合的抵抗)起作用,即便其力量被称为权力、支配、秩序等不同的名称。「地域社会论」所注目的是这种「场域」的运作方式。
这个「场域」可比喻成把个体(单字)连繫起来的句法乃至「文法」,而被人们共同认知并通行的领域。「地域社会论」把这个领域从原先特定空间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试图重新解释为更柔软且可变的结构,也就是藉由人与人连结关系为网目,并以共有目标作为基础而成立的认知体系,才始赋予其根据,并且具有从内部逐渐充实的结构。
从这个摘要中浮出的「社会」的想像,并不具备清楚的轮廓,甚至可能让人感到是非常模糊不清的。然而,正是这样的不定型的特性,才让我受到「地域社会论」的吸引。(三之三:摘自时报文化《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更多精彩内容请免费下载《翻爆》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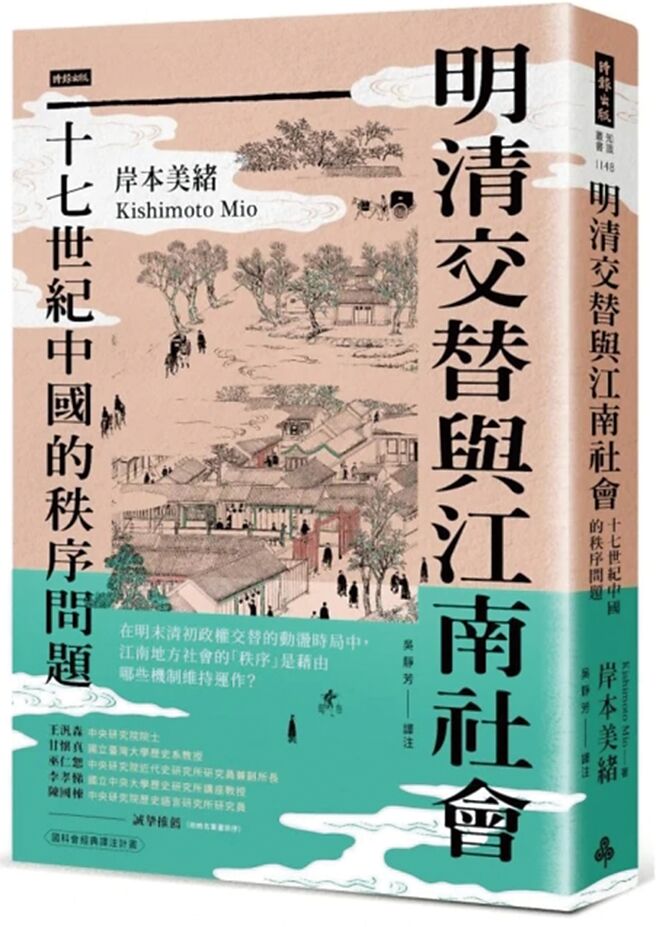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