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如果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威廉.莎士比亚)
《玫瑰的名字》是义大利着名的符号学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32~2016)于1980年出版的第一本长篇推理小说;成书四十余年,已被转译成多国文字,并且歷久不衰。其中除了扑朔迷离的连环谋杀案与惊险奇诡的破案过程可媲美《达文西密码》之外,全书更充满着深邃的宗教哲理与繁复的神学辩证。
其实,这也是一本歷史与虚构交错铺衍的小说,故事的时空背景设定在艾可专精研究的十四世纪欧洲。一个博学多闻又擅长逻辑推理的方济各修士威廉,为了调解当时的皇权与教权之争,带着年轻的见习僧阿德索造访当时拥有全世界最多藏书的本笃教会,却意外遭逢院内骇人的几桩谋杀案。儘管受托调查的威廉锲而不舍,终于解开一纸神秘的符码与禁书之谜,也抽丝剥茧地推论出不同凶手的动机与匪夷所思的作案手法,最终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吞噬图书馆,所有珍贵的藏书与宏伟的教堂建筑,皆在延烧的烈焰中付诸一炬。
此书曾在1986年被改编为电影(或译《蔷薇的符号》,由当时的巨星史恩.康纳莱饰演满怀正义、思想开明的威廉修士。)为了吸引观眾,剧情强调的仍是悬疑与推理。然而,依作者所言,这本将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重点应是「书的故事」。(艾可认为书本是有生命的,它们能彼此对话、诠释,或为互文。)而小说中致命的争端纷扰,除了滥觞于中世纪眾多教派之间的教义分歧,彼此党同伐异,亟力将对立的宗派贬斥为异端邪说,以及教廷与皇室之间明争暗斗的高层权势角力之外,更是肇因于何人才能享有阅读资格与诠释知识的歧见。
而这恰是当时欧洲社会分崩离析的乱象,也是真理与信仰、开明与保守,各执己见又难以跨越的鸿沟。在主堡的密室「非洲之末」里收藏着许多禁书,其中又以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第二卷孤本最为珍贵;却也被以卫道者自居的盲眼老修士佐治视为动摇基本教义、影响年轻僧侣思想认知的大毒草。然而,愈是禁制,愈是激起更多人想一窥其中奥义的好奇心,以致引发修道院内连串的横死悲剧──知识即是力量,可若遭误读曲解,无论以语言文字或图像符号呈现,皆能形成非理性的集体意识或潜意识,终至逆袭反噬,自伤伤人。在藏书宝库的锁钥终于被开启后,固守己见的佐治竟不惜决绝地毁书殉身,又推倒油灯,让整座图书馆与修道院陷入火海,也让满室手抄本的古籍沦为现成的助燃物……火舌熊熊高窜,所有纠葛无解的是非善恶,所有虚拟的妄想与猵狭的执念,尽在炼狱般的炽焰中灰飞烟灭。
无可讳言的是,对一个非教徒而言,阅读这本文学鉅着的最大考验,不仅是中世纪山头林立的宗派教义;其中因作者旁徵博引而多达三百多则的注释(新版甚且另附一册注本),更是阅读者的「障碍赛」与挑战。所幸小说叙事皆为直线进行,依循每日祈祷的时段顺序推衍;即便略过部分注解,也不难在作者鉅细靡遗的场景描绘与巖峻对峙的文明思辩中,约略窥知艾可亟欲建构或拆解的、一个多元多变的哲学宇宙──有趣的是,此书近日更由义大利插画家米罗.马那哈出版了彩色漫画版,将艾可笔下细腻描述的教堂大门山墙上繁复的浮雕、阿德莫泥金彩绘的异想世界,以及曲路迷宫般的主堡密室等,化为具体图像;也让读者藉由一幅幅生动的绘画,再次应证自己在阅读书中的精采文字时,脑海里同步衍生的画面。
此外,做为呼应书名的结语:「昨日玫瑰徒留名,吾等仅能拥虚名。」(注)也明确揭橥了此书的主旨与意涵。物换星移,数十年后,当年迈的阿德索回到修道院原址,目睹荒烟蔓草中的颓圮废墟时,更深刻体悟人世不过镜花水月,从喧闹到虚无,终究徒留回忆的不胜欷歔。
只是,除了做为符徵的唯美表象,玫瑰即便萎谢,零落成泥,那隽永的芬芳与浪漫、和平,乃至螫刺的多重意象,依然永存识者心中。阿德索在废墟中捡拾了劫后残存的断简残篇,并竭尽余生之力,将早年的奇遇与悲喜忧欢尽皆撰写成书,无非是为了见证那个扰攘的时代,记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与积极求知的心路歷程(也为年少轻狂的情欲悔罪救赎)──这其中,或许也含括了熟谙符号学的作者留给读者不少自行解读的言外之意吧。
*注:旧译:「昔日的玫瑰,仅存其名。」英文版翻译:”The rose of old remains only in its name,we possess naked na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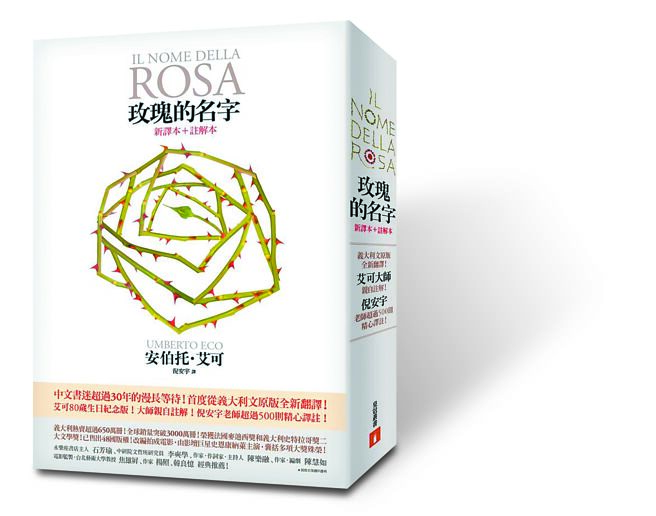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