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时间,嘉琪总坐在教室外那张椅子上。小小的身影孤独无助,两手垂放腿边,像搁置的一段旋律,不再流动。阳光从树叶缝隙中撒落,在她身上留下一片沉默的光斑。
她的眼睛总是流动的,偷偷地,缓缓地,扫过每一个奔跑的身影──孩子们追逐、喊叫、翻滚,笑声像潮水一波波向外漫开。那些声音似乎与她无关,却又像在哪里出现过,在她的梦里。
每一次,我的内心都如针扎过,忍不住想抱她入怀,但是迟疑许久,不敢靠近。不知是怕惊扰她那近乎透明的沉静,还是害怕自己也无法进入她的沉默世界。
她不是一直这样的。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她就醒了,蹦蹦跳跳地跑来和我与士杰说话,唱歌、说笑、自编自演,家里到处都是她银铃的笑声。可是,当我们牵着她一走进学校大门,她就像忽然被抽掉了电源,整个人僵硬,声音卡进喉咙深处,再也出不来。
一年多来,日復一日,固定的变奏曲,家里的她喧闹、快乐,学校的她,安静沉默如影。老师同学和她说话,她怯怯看着他们,说不出一个字,直到他们都诧然失望离开她!
曾有人说她害羞,长大就会好。有人建议多让小朋友来家里玩,有人说要常带她出门,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是她的沉默依旧,像一道高墙把老师同学都排阻在外。
我记得那次学校活动,小朋友们上台合唱,她独自站在台下。老师似乎哄着她,可她只是僵着,眼神空空地望着台上。我远远看着她沉寂的脸,内心滴着血,为什么她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轻松地站上台、放声歌唱?
夜深人静时,我曾问她,是否想和同学一起玩。她猛点头,眼睛闪着热烈的光芒。她其实观察入微,懂得同侪间所有的游戏规则。和我们玩时,常常激动得像海豚尖叫,那些她在学校压抑住的语言与情绪,会在家里爆炸开来。
我们像无头苍蝇般四处求医,得到不少诊断,学了许多名词,却始终无法厘清她那坚如磐石的沉默。直到某晚,我在脸书社团上看到一篇贴文,一位远在德州的母亲讲述她女儿与沉默搏斗的故事,终于看见曙光。
我看着看着,眼泪静静落下来。原来不是只有我们。原来,沉默也有名字,「选择性缄默症」。原来,也有人,走过同样的路,仍愿意转身拉别人的手。
我鼓起勇气写讯息给她。她立刻回信说:「孩子不说话不是一种选择,是因为焦虑的身体状况开不了口。其实他们一直在对世界说话,只是别人听不见。」她教我怎么陪着嘉琪一起呼吸,怎么不问、不催、不逼,只像阳光一样,陪伴在她身边。
我复制她分享的心路歷程,让嘉琪从「挥手」向老师同学再见开始,如果成功就能得到贴纸,日后换取礼物。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从「肢体动作」到轻声细语的「再见」「明天见」。这样微小的目标于她却是踏出舒适圈艰难的一大步。
我问她,跟老师、同学道再见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她说:「有点害怕,但也很开心。」
现在的嘉琪,还是不说话。但她会用注音写小卡片给老师、同学,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些改变很小,小得像晨光中一粒尘埃。但对她来说,是走出沉默的步伐,是对世界轻声说:「我在。」
我不再问她什么时候会开口说话了。因为我终于懂了——声音不是唯一的语言。沉默的孩子,也在用他们的方式爱着、回应着。
我们能做的,不是推他们一把,而是蹲下来,等。像春天等花开,像夜晚等星辰,像母亲,等一个孩子自己走过来的那一刻——带着她那份沈默的勇气。
附注:选择性缄默症不是「害羞」「不想说」「没礼貌」,而是「让孩子在某些社交场合完全说不出话来的焦虑障碍。」
这个病,直到近十年才被正确认识,很多人以为这是孩子的「个性」、是「父母教养的失败」,其实那是孩子正在努力挣脱恐惧的牢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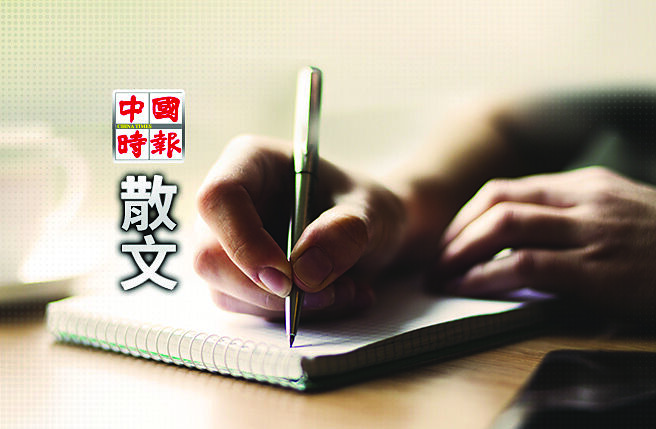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