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中在白色恐怖、动员戡乱之下仍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就在觉楼各个社团的办公室里,不受许多校规的拘束。当时校规规定男女不能并肩行走,可是在觉楼里,不存在这些思想和行为的拘束。
我进入板青之后,总编辑杨正华打算在校刊制作一个选举的专题,讨论选举和政党政治的种种问题,我被指定协助这个专题的编写。为了写这个专题,我到光华商场和《联合报》社找资料,在这过程中认识了《自由中国》,也因此接触了雷震、傅正等歷史人物资料。这对我现在的法政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开启了我蒙昧的双眼。
当时校刊的编辑风格,35期到37期都是由学生主导,和前后由学校教职员主导者,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举例来讲,35期的校刊封面是学生手绘的一条蟠龙缠绕着象徵「35」的巨柱,内页则进一步延续龙的主题,学生手绘的蟠龙蜿蜒成万里长城,学生诗吟在其上题写「龙的传人」4个字,学生的书画都很好,但用跨页来刊登他的作品,做法上也很是大胆。
那几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外有台美断交的衝击,内有政府对党外反对运动的镇压,这个封面表现出学生知识份子对于国事的忧思与自许;36期是杨正华他们到摄影棚拍的,板青男女生的手争抢一份手稿的照片,握着稿件的手充满自信地高高举起,你可以看到板中青年的意气风发;37期的封面则是叶荣文的作品,象徵热血的鹅卵石围着一叶新绿的菩提,你看到板中青年对生命的热情。
那些鹅卵石是叶荣文、我和何荣幸到台北市外双溪河边去捡的,照片也是在摄影棚拍出来的。至于那前后的34、38期,封面则都是慧楼,拍得端端正正,但毫无生气。
参与校刊编辑主要是在高二时,当时我的功课被当得乱七八糟,但是人生很长,不必在乎那一年、两年、那几个月,不必在乎3年内一定要考上大学、学校升学率如何。教育是百年树人,要让学生从中自省认清人生方向,不要迷惘。时间到了,他自己会振翅高飞,自行觅食。我在社团活动中,体会到这一点。
当时学校有个编制叫「安全维护秘书」,专门负责校园里的思想管控,后来张镇民校长从省立基隆高中调来板中,他让安全维护秘书尤文治充分发挥东厂的功能,最后终于对校刊社同学们开刀。我母亲在我六叔陪同下亲自到校了解经过并要为我求情,我们全家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我当时并不了解为什么父亲不愿出面处理,后来才知道他年轻时曾经受到政治迫害,担心旧案被掀出反而害了我。
我的母亲既恐惧又勇敢,她被尤文治质问道:「妳知不知道妳的小孩在看什么书?」我母亲回答说:「读大学联考要看的书」,安维秘书反驳道:「他有看过鲁迅」。「看过鲁迅」成为一种思想问题,说实在的,这种校园气氛的转变,我完全无法适应,很多同学也很难接受。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兼任副教授)
【未完待续,曾建元专栏每周五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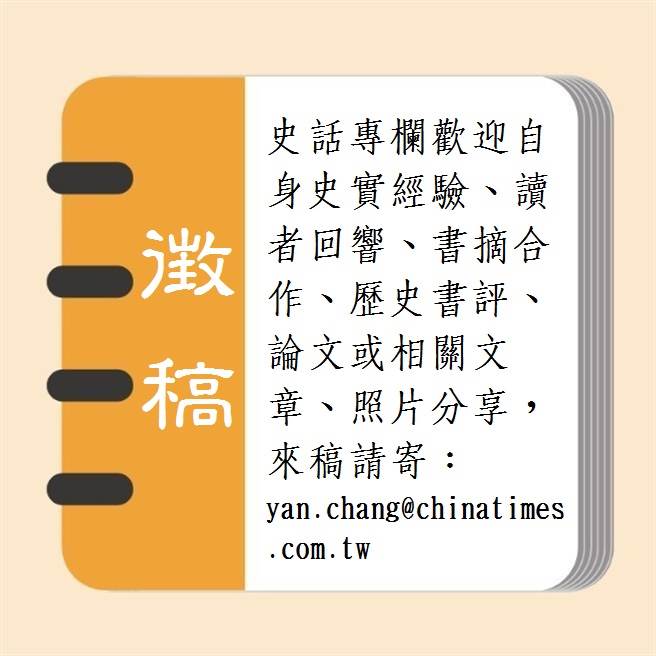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