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22年5月,德语剧坛的年度盛事——柏林戏剧盛(以下简称盛会)再度以实体展开。两篇自柏林传回的现场报导,除了带我们深入了解,后疫情时代欧陆关注的剧场话题。另外,透过专访即将卸任的总监伊冯娜.巴登霍尔(Yvonne Büdenhölzer),充分认识盛会这11年来如何带动剧场讨论,使其成长为如今国际化、推动女性平权的剧场重要指标。
柏林戏剧盛会(以下简称盛会)在受疫情影响发展全数位线上版本,经过两年以后,2022这一年,终于回归实体活动。现场活动气氛热络,即使主要场地柏林戏剧节之屋(Haus der Berliner Festspiele)仍在进行外观整修,整栋建筑物还包裹着鹰架与白色塑胶布,却仍浇熄不了柏林人参与盛会的热情。演出前后许多观眾聚集在花园广场交流意见,人潮久久未散去。
彷佛是卸任前的最后一搏,盛会总监伊冯娜.巴登霍尔和其团队在引领议题讨论上下足功夫,不仅10大「最受瞩目」(bemerkenswert)作品扣合时事,剧本市集(Stückemarkt)也以策展主题「(我们)何去何从?」(What is the future worth (to us)?)选出多个(反)乌托邦主题的作品,巧合地呼应乌俄战事。同时再次与拯救世界协会(Save the World)共同策划「焦点议题」(Burning Issues)活动,讨论平权问题。而「盛会论坛」(TT Kontext)则分享德语区重要剧院为永续发展付出的努力,也检讨现行制度下的问题。
如何说服观眾走进剧场成了课题
后疫情时代,德语区剧场的指标——戏剧盛会,也必须适应新的日常,不仅得承担演职人员染疫临时取消演出的风险,还要和各种家用串流娱乐平台竞争。文化评论人托比.穆勒(Tobi Müller)于《南德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发表〈泡泡里的衰败〉(Schwundstufen in der Bubble)文章中指出,观眾的消费行为受到疫情影响改变,不再对用议题包装的剧场作品买单。的确,无论专业观眾或路人游客,德国观眾们开始重新思考进剧场的意义。这同时也考验创作者和艺术节团队,该如何说服观眾,作品值得他们付出一个晚上的专注。
在此氛围之下,7位评审从大约400个德语作品中,挑选出10部展现时代精神的重要作品。当中不少作品兼具娱乐和思辨,运用音乐、舞蹈来转译文本的作品也较以往多,最明显的是喜剧且充满歌舞的作品,占今年入选作品中的3部:《偽君子,或是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Der Tartuffe oder Kapital und Ideologie)大幅改编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经典名着、《滑稽斜坡》(Slippery Slope)(注1)用流行音乐产业的虚构明星故事讨论取消文化、《人文主义者啊!废除分裂》(humanistää!– an abolition of divisions)(注2)以音乐剧场来解构诗歌、富含多层隐喻,反思文字、文化和体制的僵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偽君子,或是资本主义和意识型态》,将时空背景搬到1980年代经歷柏林围墙倒塌的德国。原着中骗子主角答尔丢夫摇身一变成为打着资本主义旗帜的骗子,以高额借贷欺骗毫无资产的民眾买下幻想,最后失去所有。除了保留原着中的角色形象之外,文本做了大幅度地更动,使其呈现资本主义当年如何衝击以社会主义为基底的德国社会发展,也利用投影纪实新闻影像唤起大眾对歷史的记忆。
演出的最后,则藉由当代法国经济学者汤玛斯.皮凯提(Thomas Piketty )提出全球性贫富不均的问题,——督促政府和国际重要组织採取行动,鼓励坐在观眾席的每个人去思考,该如何选择才能一起迈向贫富均等的未来。
剧本市集选出象徵多元世界和环境的作品
剧本市集则从全世界61个国家、357件作品中,选出最后5件作品。总监安娜-凯特琳娜.穆勒(Anna-Katharina Müller)分享,剧本市集特别强调平权和找到创新剧场语言,从30位评审初选阶段,考虑的就不是作品的语言、风格、构作等,而是作品是否代表了多元文化、以及我们身处的世界和环境。
于是,评审们选出了来自克罗埃西亚的全女演员团队Igralke搬演作品《奶奶们》(Granies),以记录和编创剧场的形式将真实故事搬上舞台,藉由5位捡拾宝特瓶回收以换取现金的退休妇女,探讨克罗埃西亚妇女退休金制度中的不公平,导致65岁以上的妇女无法在退休后获得生活保障。作品首演不久便获得女权记者博雅那.古伯拉(Bojana Guberac)的报导和左翼国会议员达拉.波里其(Rada Borić)的关注,与团队讨论未来也可能将作品带到议会展演。
从5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莱比锡剧院委托制作的非裔英国女性剧作家阿曼达.威尔金(Amanda Wilkin)则以《而我梦见自己被淹没》(And I dreamt I was drowning)讲述难民逃离强权控制的社会,反讽英国政府对难民的不欢迎,也透露政策对人民造成的剧烈影响。其精神呼应莱比锡剧院发展于前东德的歷史脉络,因此获得青睐。
剧场仍旧是提供人民思考和讨论的场域
从白天的论坛讲座到晚上的作品展演,盛会所有议程及演出顺序的安排都彷佛在宣告:庆祝后疫情时代的劫后余生,并且一同思考未来我们要往哪去。入选作品中在在发人深省,不仅有如《男人与他的阶级》(Ein Mann seiner Klasse)提醒观眾不要忽略社会底层的贫穷,重新检视现有的体制结构。《圣女贞德》(Die Jungfrau von Orlenas)希望将多数人从父权结构中解放,《像恋人一样》(Like Lovers Do)提醒大眾不要再隐忍那些以爱为名的性暴力。现实生活中,多元平权、永续发展和贫富阶级都还需要我们去行动,做出选择与改变。
面对作品的选择,部分文化评论人似乎不太买单,如克里斯汀.朵尔赛(Christine Dössel)于瑞士新兴媒体《共和国》(Republik)〈战争时刻的剧场——对柏林戏剧盛会的印象〉(Theater in Zeiten des Krieges)一文写道,这些作品「品味精致小眾(Niche),是一群被过度保护的书呆子菁英在剧场泡泡里做出的选择」,或者托比.穆勒认为今年10件入选作品的政治意涵似乎远大于美学意义。此届评审也在最终公开论坛中回应这些评论,认为他们在选择作品时乌俄尚未开战,也许是因为创作者回应当代社会提出的质疑,并在作品中寻找答案,才使得入选作品反映时代精神。
剧场之所以独特,正是因为它能够创造一群人在一个特定时空里的交会,在看完作品带来的思辨,理解社会如何运作,提醒大眾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又该如何做出选择。面对外界争议,盛会也始终未放弃剧场扮演的社会性功能:作为提供人民思考和讨论的场域。对于观眾而言,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剧场吗?
是的,永远需要。
(注)
1.《滑稽斜坡》为2016年来台臺演出《共同境地》导演雅叶.洛能(Yael Ronen)的最新作品,由柏林高尔基剧院(Maxim Gorki Theater)制作,以洛能一贯幽默反讽的风格贯穿全剧,玩味反转百老匯音乐剧的形式。
2.《人文主义者啊!废除分裂》戏名改编自奥地利作家恩斯特.扬德尔(Ernst Jandl)的诗歌作品《来自异乡》(Aus der Fremde)。《来自异乡》是扬德尔以第三人称诗歌体描写他和文学家伴侣费莉德丽克.梅罗克(Friederike Mayröcker)爱恨交织、相互牵制的同居生活。
疫情下的盛会讨论
解封许久的德国,防疫措施松绑许多,普罗大眾也将新冠病毒视为一般感冒病毒,继续如常生活。演出当天若有演员确诊,剧院和团队就得立刻决定是否照常演出。今年盛会中唯一更动的节目是《圣女贞德》:由首次入选盛会的波兰女导演艾薇琳娜.马基尼雅克(Ewelina Marciniak)改编《圣女贞德》原着,结合经典电影影像、动作设计等美学来解放父权结构底下的圣女╱处女形象。柏林首场演出当天,一位演员确诊,剧团最终决定改以90分钟影像版和20分钟的现场版本一起呈现。总监巴登霍尔说明,这完全是基于艺术考量,当天也有近9成观眾留下来观赏演出。
因应疫情的临时变动,还是给自由工作者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盛会论坛」中策划了题目「永远如此?」(Forever Present?)讨论德语区剧场整体受疫情影响的现况,导演海格.舒米特(Helge Schmidt)就分享,大多数剧院和自由工作者还是经常担心演出或工作被取消,这样的不确定性影响许多剧场人思考,如今的体制是否出了问题,是否仍然值得自己付出大量的心力投入。
在「盛会论坛」其他系列讲座中,不少与会嘉宾也都提到针对疫情,体制需要做出的改变,比如调整补助方针、增加数位内容等,如今几乎大部分剧院都有数位资料库,而盛会更是录制完整讲座内容收录于媒体资料库中免费供大眾浏览。
另一个需要改变的重点则是永续发展,比如妥善回收资源再利用,也尽可能使用友善环境的材质。多位嘉宾都呼吁,期盼政府能够正视疫情影响和永续发展的相关问题,并确实立下规范来推动更加全面的变革。
本文作者:王颢烨
(本文摘自《PAR表演艺术7月号第34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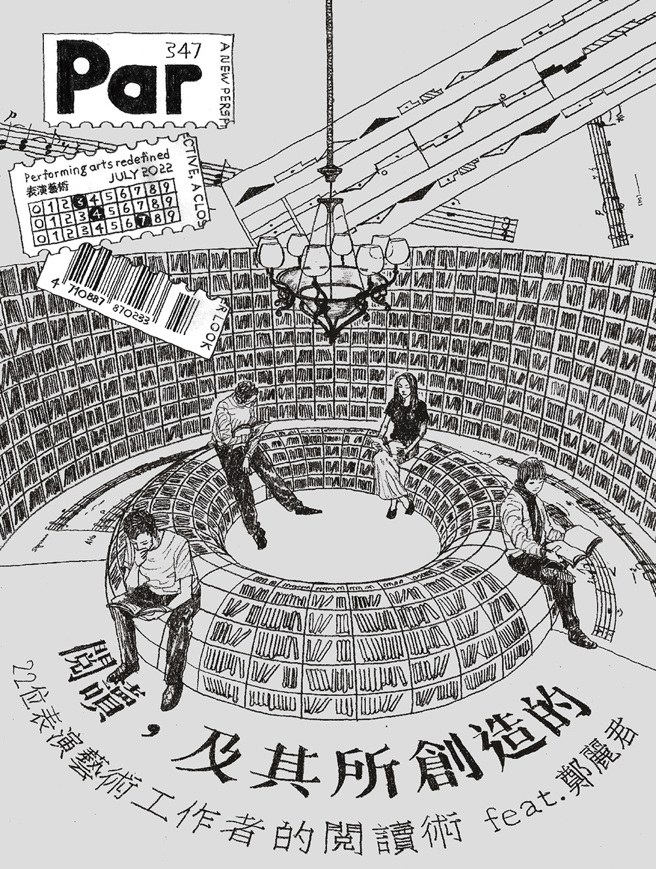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