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欧元兑美元贬破1比1大关,创20年来最低纪录。欧元兑美元曾达到1比1.6,如今从最高点重贬6成。欧元何以至此?
最关键的致命伤,就是欧元区各国个别经济实力差异过大,偏偏要如「两人三脚」的游戏绑在一起走,结果不但走得慢,也走不稳。
但说来讽刺,欧元建立的动心起念,其实是寻求货币稳定。
深受石油危机等多次利空衝击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决意建立一套属于欧洲稳定的匯率系统。歷经万难,欧元总算在1999年正式上路,起初为虚拟货币,直到2002年,才开始发行纸钞和硬币。
欧元要求会员经济力一致
成热门避险货币、攀上高点
欧元流通最重要的大原则被称为「趋同标准」(convergence criteria),它要求加入的会员国须达成一定的通膨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比率、长期利率和控制匯率能力,也就是说,会员国的经济能力必须差异不大。
这样的理念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的孟岱尔(Robert Mundell)。孟岱尔的理论指出,若多个地区要使用共同货币,条件之一是经济状况必须相近,如此才能最大化经济整合的效益。
这些建立欧元的高标准,在欧元正式问世的头10年(1999年到2008年)起到一定作用,堪称该货币的「黄金10年」。
这段期间,各个会员国财政纪律良好,欧元竞争力上升。而且,自2005年起,美国一路经歷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国际对美元渐失信心,欧元因而成为更理想的储备货币和避险选项,欧元迎来一波长期的升幅,在2008年4月,兑美元匯率站到了1比1.6的歷史高点。
「如果欧元有天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或成为同等重要的储备货币被交易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连美国重量级经济学家、曾5度续任美国联准会主席的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都在2007年盛讚欧元。他认为,欧元的稳定让它逐渐被广泛使用,加速该区的经济发展。
制度僵化酿欧债危机
弱国丧失主导权被负债拖垮
但是,葛林斯班错了,欧元高升的声势没有延续,反而急转直下。
2009年底开始,经歷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后,欧洲多个国家,例如希腊、义大利等国,出现财政赤字和负债攀升的危机,烽火四起。最严重的希腊,其公债评级在短短几个月内被标准普尔从A-降到垃圾级别的BB+,开始爆发「欧债危机」。
欧洲央行无力解决欧债危机,令市场对欧元开始起了怀疑,不仅欧元占国际储备货币比率逐年下降,兑美元匯率也一路从2009年底欧债爆发前约1.5的高点,在隔年5月贬到约1.2,半年内重贬20%。
而且,欧元竟然也是压垮希腊等国经济的罪魁祸首之一!
当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在《失控的欧元》一书中指出,欧元的设计让成员国丧失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无法即时回应经济危机,例如贸易赤字攀升的希腊没有办法透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
相较下,史迪格里兹认为,美国各州之间虽然差异也大,有穷有富,但因为各州保有充分制定利率的权力,且联邦政府有充沛资源可援助面临危机的各州政府或银行。这是欧盟无法比拟的,因此欧盟通常会要求成员国为自己的银行负责,不像美国会由联邦政府出面主导。
「趋同标准的设计却导致了趋异(divergence):当面临负面衝击,强国牺牲弱国而获益。」史迪格里兹在书中指出了欧元失控的核心。因为面对经济危机,严格的趋同标准,有利欧洲强国德国,得以保持高额贸易出超,却让希腊等弱国,持续遭遇逆差,最后让欧元区里「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欧元制度是欧债困境的根源,」曾任总统府资政、台湾知名经济学家陈博志也曾撰文指出,因为欧元制度把抑制物价做为首要目标,却因此限制欧元区各国政府调整金融供给的能力,共同匯率也难以符合个别国家需求。
连支持欧元的学者,都出面建议欧元制度需要改革。
孟岱尔在2012年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出来信心喊话,认为欧元将安然度过经济动盪,而欧元的问题在于「太强,而非太弱」。但他建议欧元区应该要尽快成立联合银行体系,以及欧元债券与国库券,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他们仍须重写欧元区的比赛规则,并完成这栋盖一半的房子,」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办人柏格斯滕(C. Fred Bergsten)认为欧元将会生存下去,但必须改变。
欧洲央行决策慢半拍
疫情、通膨都错失出手良机
欧债危机的余波荡漾,更揭露欧洲、美国的差异:欧洲央行偏重经济稳定,决策慢;而美国联准会重视经济发展,决策快速。
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联准会早已进行多次量化宽松政策,带动经济强劲復甦,甚至2014年已准备升息,压抑过热的经济;反观因债务危机导致紧缩多年的欧盟,深怕松垮的财政纪律会再次酝酿新的债务危机,拖到2015年才开始全面发动量化宽松(指购债计画,利率约从2012年开始调降)。
一升一降,美、欧元的利差拉大导致2014下半年欧元的一波大贬。欧元兑美元匯率贬入1.1到1.2左右的区间,从此再也没爬回去过。
歷史总是一再重演。2020年至2021年,COVID-19重挫美国经济,美国联准会迅速把利率降至趋近于零(此时欧元区仍维持负利率),放贬美元提振经济;相较下欧元区论经济和防疫表现都较佳,欧元兑美元因而小幅回升。
但2021年之后,疫情缓和,经济开始復甦,通膨危机开始引爆,美国在今年3月开始採取升息措施,包括台湾在内,各国央行也纷纷加入升息行列以因应通膨。然而,即便通膨严重程度不亚于美国,欧洲央行却像慢半拍一样,迟迟不敢动作。
而且,祸不单行的是,今年2月底俄罗斯、乌克兰爆发战争,俄罗斯是欧洲的能源出口大国,更让欧洲头痛万分。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今年4月时表示,欧洲通膨5成和能源价格有关,「我今天调升利率,也无法把能源价格压下来。」几经波折才敲定预计于7月下半旬升息1码;而美国今年以来已经升息6码,7月底可能会再升3码。
令拉加德头痛的还有义大利高攀的债务,若升息过快可能会再次引发债务危机。虽然她在6月的央行会议表示,目前已在制定新的工具对抗债务问题,避免当年危机重演,但欧洲央行至今仍显得左右掣肘,对各国间巨大的差异没辙。
多年来美元虽然有上有下,称不上「稳定」两字,但面对危机却能展现更强韧性;相对以「稳定」为首的欧元,面对重大危机时却难以迅速应对,反而容易酿成更大的动盪。
欧元区好像一家公司,里面人才有强有弱,却硬加诸同一套标准在所有人身上,但有些人跟不上就是跟不上,导致管理层左右为难,迎合强者会逼弱者倒下,但为弱者放宽标准又会拖垮公司信誉,最终处处受制,难以作为,这间公司只能一起沉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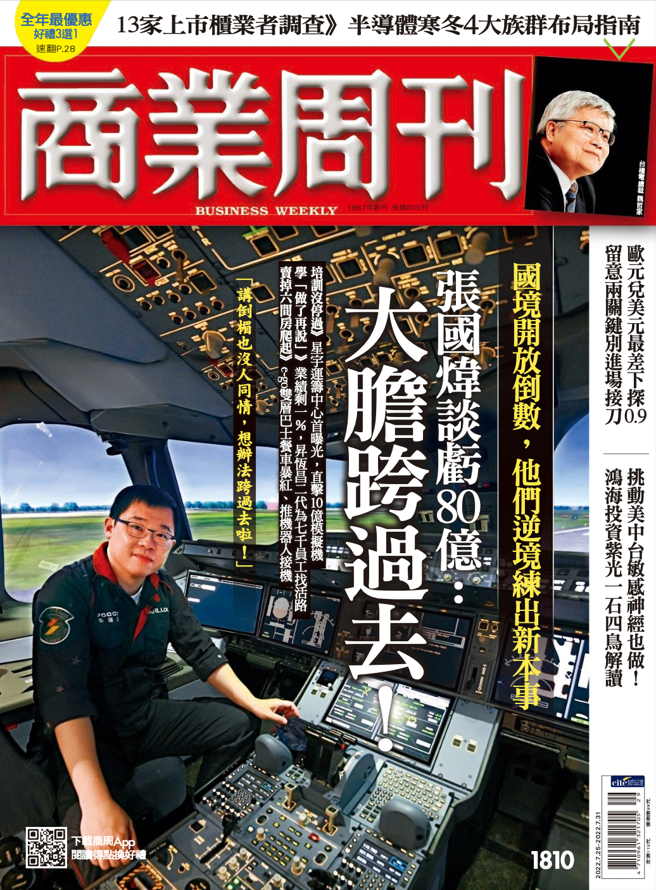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