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界持續上下流通,也為書寫帶進門來下層世界的人,書寫有重重門檻,但沒這種勢利眼。文學極可能是人類所有行當最不勢利的一種,來自下層世界的新書寫者,如果夠好(並不苛刻程度的夠好),並不被排斥,反倒是直上C位的驚喜,彷彿把原有的文學圖像「刷新」一次,還往往得到超過真正評價的注目和讚譽,俄國的果戈里、契訶夫是如此,日本的林芙美子爾後也如此。
只是,這比想的要慢、要難。
首先,要有足夠數量的下層世界之人能熟練掌握文字,從中冒出來夠格的書寫者,這是等於要讓整個世界脫胎換骨一次的人類大工程,沒個幾世紀耐心是做不到的。
固然,個體有超越性,不必等待集體齊一完成,甚至,我們可以相信波赫士說的,「每一人的一生,都可以寫出一本極好的書」(亦即,人一生夠厚夠重,材料上絕對夠)。事實也是這樣,足夠強的生命素材,對文字技藝的依賴可以降到極低,所以起步即顛峰,第一本書用的總是生命中最珍貴最厚積的材料,甚至如賈西亞.馬奎茲說他自己寫的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總以為這輩子只寫這本書,恨不得把自己所知的一切都用進去。」不只來自下層,時至今日小說世界從不間斷出現所謂的素人小說家,且往往第一本書就是他最好的作品,至少不出前三本,這個現象如今在通俗類型小說是通則,不這樣才是例外。
原因可以極直接說。人的生命經歷,就一本書而言太多,但對一生的書寫則又少得可憐,兩本三本就差不多空了,所有認真的書寫者都可證此為真。寫下去,書寫的重重門檻這才一個一個來,感性生命材料的快速消耗,得由人的思維、以及文字技藝來補充來替換。因此,「讀」和「學」變得比「寫」更重要;也就是說,書寫得是專業了,所謂「素人」只是暫時性身分,不轉入專業,就得離開。
你當然也可以同時是礦工、同時是書寫者,這可能但不切實際,也難以持久,借用葛林的話說,「你遲早要選一邊站的」。
就來自下層的書寫者而言,更直接的難題是,如何取得這個「有錢有閒」的書寫位置,或平實的說,如何同時擠出足夠的物質條件和時間,這無疑還早,現實世界還差得遠。
因此,小說向大眾傾斜、翻轉,不是走書寫之路,而是閱讀之路—做為讀者,遠比做為書寫者便宜、省時間,而且識字即可,但即使如此,也還是得費時幾個世紀。
在笛福.費爾丁當時,工業革命才起步,書籍是極昂貴的,就連夜間照明的蠟燭都算奢侈品,如中國古時的窮書生得靠雪光或螢火蟲微光,甚至冒著痴漢罪名鑿牆壁來偷。換算,彼時一本書的價格相當於一個工人兩個月的工資,也就是說,相當於今天用六萬台幣來買一本書,這讀得下去嗎?所以,很長時日,在這個下層的勞動世界,閱讀一直被看成是「有害」的,敗家、浪費時間而且徒亂人心,讓人上不上下不下無法安分於生計。
閱讀,緩緩的以某種蜿蜒的、滲透的方式進行。像是,買不起書的人讀可以傳看的廉價報刊,上頭印有連載的、當然多為享樂成分較高的小說;同理由,小說也拆冊出版,如我們熟悉的分期付款概念。此一迢迢長路,甚至一直延伸到我這代人的童年,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左右的台灣,買書依然是得下點決心的事;更多人通過報紙副刊連載讀小說,如歷史小說是《聯合報》的高陽和《中國時報》的南宮搏,武俠小說是《聯合報》的臥龍生和《中國時報》的東方玉云云;武俠小說也仍拆冊出版,一部武俠可拆到四、五十小冊,且不由購買、而是從租書店租來;此外,閱讀有害論仍餘音裊裊,尤其讀小說,通常得躲著父母和老師。
美國的冷硬私探小說,也是從彼時的《黑面具》雜誌開始刊載,包括其代表作,漢密特的《馬爾他之鷹》。
此一長路途中,至少有這兩個重要節點—一是、所謂「讀小說的廚房女傭」;另一是、企鵝出版社的「六便士小說」。某種意義來說,是前者促成了後者,真正改變了人類世界的閱讀風貌。閱讀(小說)如打開缺口的流向下層世界,開始於廚房女傭而非一般勞動者。女傭畢竟是彼時最貼近上層世界的人,她可由女主人處借來小說;之前,她從主人和其友人的交談就先聽到有關小說種種,有相當的閱讀準備,她也有燈光,晚飯後的休憩私人時間,廚房一燈如豆,但足夠她看清書上文字—
六便士小說,一本書可用一包菸而不再是兩個月的工資取得,小說閱讀至此才真正開向一般人,而這已經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價格╳數量=營業額,最簡明的換算公式,低價當然是閱讀的福音,但愈是影響深遠的大事,總愈有著某種潘朵拉盒子意味的種種效應,你打開它,不會只跑出來單一一個東西。書價可壓這麼低,便得以數量的大增為條件;也就是說,數量從此成為小說成書的一個大門檻,而且,數量的命令聲音,會愈來愈響亮愈堅決,書寫者多出來一個得小心侍奉的神,還是一個不怎麼在意品質、偏感官享樂的神。你怎麼可能只要這邊不要那邊呢?(本文摘自《我播種黃金》一書,印刻文化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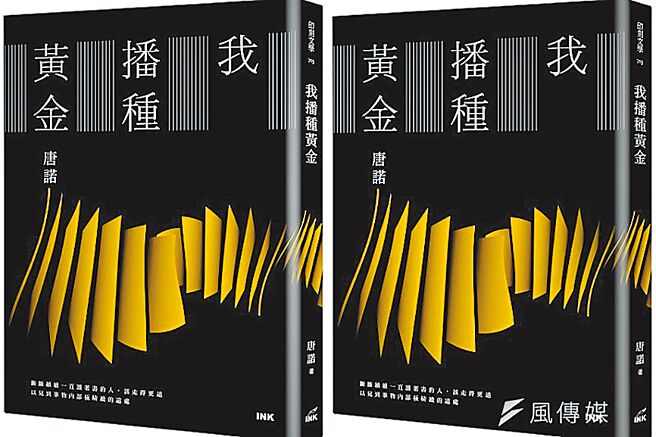
發表意見
中時新聞網對留言系統使用者發布的文字、圖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權利。當使用者使用本網站留言服務時,表示已詳細閱讀並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規定:
違反上述規定者,中時新聞網有權刪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鎖帳號!請使用者在發言前,務必先閱讀留言板規則,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