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就是二十年流光如咒语,不知怎么就把人抛到了后面。回想起来,少年的学生与中年的我,彼此教学相长,在人生路上紧密共行了一段,对双方都成了无可分割的记忆。
那时我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在大陆招生,以北京、上海、广州的酒店会议室为据点,而参与招生的教授们第一次以视讯的方式在香港校内面试。那曾是多么新鲜的经验!我们在一座新起的教学大楼里等着广州那边连线,电脑开着机:看见酒店了,看见中大的工作人员了,看见面试的房间了,看见年轻的学子一个个进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她在答问之间条理特别清楚而口齿分外清晰,我因这个聪慧的学生而感到高兴时,一位同事突然问,除了中大有申请他校吗?她说,也可能试试澳洲的大学。开学时我心里多希望她能选我们,而又真的在课堂上看见了她,得一英才而教之的快乐竟瞬间涌上了心头。她是叶嘉。如此,我们结了这一世的师生缘。
大一下学期她修读我的翻译史,我一般从五世纪的佛经翻译讲起,一直要讲到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并兼及延安文艺讲话所揭示的文艺政策对翻译的影响。时间跨度既大,所涉议题又多,期末报告在选题上多有可发挥琢磨之处。然而叶嘉竟另辟蹊径,问我可否讨论《源氏物语》的两个中译本。我们二人都不懂日文,遑论十一世纪的古典日文。但她既有此一问,想来一片心思正在丰子恺与林文月的两个译本上,我实不想消耗这能量,何况真懂古典日文的学者,根本是凤毛麟角,目前似乎还不必考虑这因素。再者,这是她进大学后的第一篇小论文,是练习曲,不是硕、博士论文的交响乐,也许现阶段我们可暂别原文,把重点放在译文的风格上,看看丰、林两位译者呈现给我们的平安朝宫里宫外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师从林文月习谢灵运诗,老师的译文,自《中外文学》连载时期即已拜读。至于丰译比林译开始得早,却出版得晚,我倒是还没有读过。留学美国时曾随日本教授念过两学期《源氏物语》的讨论课,以韦理(Arthur Waley)与赛登斯提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英译本为主。这两个文本的译文风格,给读者如我带来了很不一样的感受。即便有误译、错译、漏译,既不能掩盖韦氏译文的绝代风华,赛氏译川端康成的清冷细腻也未能为其之译《源氏物语》增添灵气。翻译学是一新兴的研究范畴,牵涉的因素很广,这一英译对照组反衬了中译某种观点,或烘托了中译某种现象,就答应叶嘉写这个题目了。
大一生叶嘉的第一篇学期报告,从林文月与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探讨《源氏物语》的女性声口。以和歌为例,纵使林译以楚辞体为主,用的最多的语助词是「兮」字,是否合适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大量使用语助词,读起来自有一种宛转绵长之意,符合一般中文读者对日本女性在说话与仪态上的认知。而丰子恺将和歌译成五言或七言诗,读起来不似日本女子,倒像是中国士人。两个译本因风格不同,彷佛呈现出两个不同的世界。叶嘉初试啼声而能有此见解,我看见的是后生来者发掘问题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翻译之为学科,自欧盟建立以来,倍速成长。在茁壮的过程中,除了文学翻译、商业翻译、艺术翻译、法律翻译等专业科目之外,课程逐渐涵盖翻译理论、翻译史、文化与翻译等。最特别的是毕业前要交出中译英与英译中各一篇四千字的译文,而选材必须是未曾有人译过的作品。翻译期间,有固定老师一对一的指导,也可以说是藉由长篇翻译的经验,来敦促学生实际练习并作取舍以解决语言转换时带来的各种问题。
我成了叶嘉英译中的指导老师。她每个星期要译上一大段,先交给我看,上课见面时我们再讨论。回想起来,这种一星期最少一小时的互动可能是最接近《论语》里的问学。那一年是2006年,她选的是住在香港的英裔作家Matthew Harrison同一年出版的英文短篇小说Queen's Road Central。这条大马路就是有名的「皇后大道中」。他是用英文写作的香港作家,关注的人情不可能与华裔港人一样。所以故事发生在中环皇后大道中的一家银行,聚焦于白领丽人与她的洋人上司之间的各层关系。这个不同的视角,带来相异的挑战,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遭遇到许多「回译」的问题,亦即很多场合必须还原至有粤语情调的中文词语,而不是心血来潮重新译一遍。在后殖民色彩浓厚的港岛中环,熙来攘往的街道上,推挤着终日恓恓惶惶的人群。这气氛、这感觉也都得译出来。
这时我留意到对翻译理论的瞭解与能做一个行文流畅的译者实在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中、英双语都好,并不能保证翻译可以做得好,关键其实落在语言与文化的转换上。这是双语之外的第三种能力。换言之,若译入语无法脱离译出语先天的束缚,从事翻译研究的人自身往往也不能免于用翻译体翻译,甚至用翻译体写论文。叶嘉一级荣誉毕业,是当届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同时也是少有的文字通达的译者。
叶嘉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因有志于未来读博士,所以进了哲学硕士的学程,而非修满学分即获学位的一般硕士。有一门翻译理论的课必修,另外一定要写一篇硕士论文。所以论文写什么,绝对是在为自己未来的研究定方向。
那几年我或同时、或先后指导三、四个硕、博士生写论文。他们有做圣经翻译的、佛经翻译的、性别因素塑造翻译的、殖民政策与香港认同影响翻译的,都是很严肃的题目。叶嘉的兴趣却不同,她对民初以上海周瘦鹃主持的《礼拜六》杂志圈为主的通俗文学很有使命感,想在这方面尽力,故来问我的看法。我之所以知道周瘦鹃,还是因为张爱玲,还曾以张氏视自己的短篇小说为鸳鸯蝴蝶派而感到惊讶。但稍微想深一层,才想到我根本没有看过《礼拜六》杂志,这本文艺杂志中原来还有很多翻译作品。《新青年》尚且补看过很多期,最少对鲁迅、胡适、陈独秀以北平为主的革命性思想与文艺氛围有些认识,上海的城市风貌与文化品味竟全然忽略了。
我们惯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好像除了唐,其他朝代都没有诗。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况且宋诗、清诗还非常出色。在八世纪已被认可的唐代大诗人王维开了水墨画一宗,为明朝的书画大家董其昌所特别推崇。可是单讲水墨能代表唐代风华吗?直至流观敦煌壁画,细览金碧山水,才能略微感知何谓盛世的辉煌。有一回在波士顿美术馆看过一个展览,展出印象派绘画巅峰时刻的十九、二十世纪的学院派,我当场就吓了一跳,因为我脑海里若想到当时的巴黎,只会想到咖啡馆、歌剧院,以及明媚的水波与阳光,好像还是主流的学院派竟早已不復存在。这是多大的偏见啊!可见后世之人若不回归原来的语境,必难窥当代全貌。何况清末民初东西文化撞击时的力道与上述所言岂乃不可同日而语所可尽言,所以非常高兴叶嘉可以补上这一时期海派的文化风景。
叶嘉在必修的理论课上交出来的论文,是探讨周瘦鹃在《礼拜六》上撮译的一部长篇小说,原文是法文,作者是Madame de Stael。周氏不懂法文,中文本自非译自法文,而是转译自英译本Corinne, or Italy,而中译的题目竟用了晏殊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既是撮译,中间牵涉的问题当然极多,但最特别的是,周瘦鹃似乎是越译越高兴,居然自己随兴往下写开来,创作了续集,题曰:《似曾相识燕归来》,直接在下一期刊出。是先有了「花落去」的译题,而忍不住要凑上「燕归来」吗?叶嘉的论文在此探讨了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十里洋场的上海在这一杂志上展现了不同于故都文士所在意的话题。原来上海通俗文艺杂志是一堆有待挖掘的矿藏,而我们对此几近于无知,叶嘉因此立志做此方面的研究,定下了方向。(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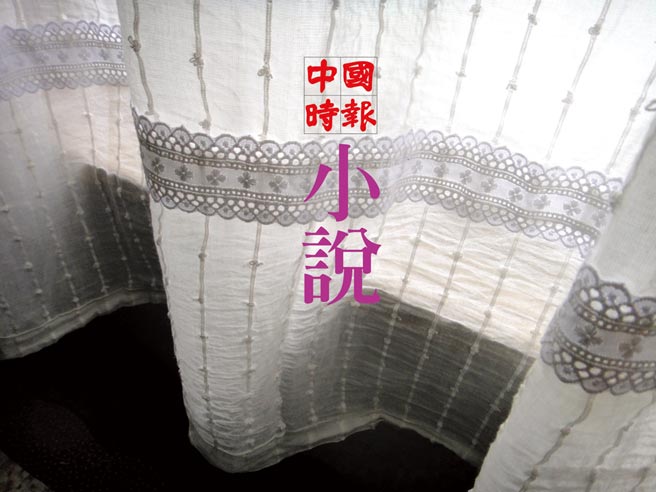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