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近期在中央深化改革会议上再度提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引起产业界与学术界热烈议论,支持者与质疑者也出现几近两极化的分歧。质疑者认为举国体制是改革开放前应对国外封锁并快速赶上技术落差的手段,在改革开放30年快速发展后再搞举国体制」,无疑是放弃改革开放政策走上回头路;支持者则认为,现在的国际情势与改革开放后大不相同,在遭西方国家的「卡脖子」策略下,只有採取举国体制是解决之道。
其实中国的举国体制政策从与苏联交恶后就出现,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也从未完全停止过。所谓「举国体制」,指的是「举全国之力」对某个特定的政策目标,不计代价与投入最大资源来突破瓶颈达成目标的「体制」。例如过去制造原子弹、氢弹、航空发动机,或是特定技术研发与大型工程,以及培养奥运重点项目夺牌选手等等。在以那个封闭与落后的年代,这么做确实也达成一些重大目标,但也付出极为惊人的代价。

这么做的动机是要在落后的情况下,尽可能集中优势力量攻克难关,而这些目标都是有关国家长远目标、战略需要与国家安全。虽然集中力量可以加快速度克服难关,但相对地代价也极大。这样的体制在选择政策目标时必然是自上而下的,由最高决策者拍板定案,加上动员大量的资源,目标当然有限,最后许多不那么急迫的、非最高领导支持的政策目标就会被迫放弃或拖延。举例来说,当年研发核弹时曾流行一句话:「寧要核子,不要裤子。」意指寧可没钱买裤子穿,也要做出核子弹,反映出为完成优先政策造成的资源挤压现象。
在改革开放前成长的大陆官员或民眾,受到这样的观念影响极深。每每在遇到瓶颈时就首先想到要动员一切代价克服难关,小至一个单位部门,大至国家政策,这种思维模式已成为大陆官僚体系根深柢固的膝盖式反应。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要搞市场经济,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就得精打细算成本与收益,这种举国体制的思考模式才渐渐被放弃。除了要求强化领导中心的官僚机构还有类似的膝盖反应外,民间社会已换上风险收益率与避险措施来进行决策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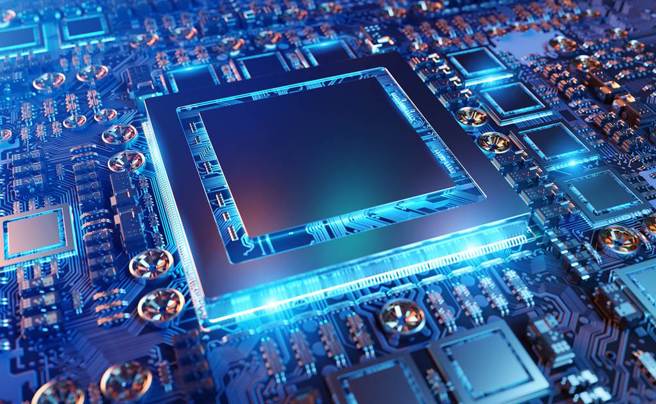
大陆改革开放30年至今,许多财经科技政策专家仍经常埋怨官场上过多的举国体制思维,其实这几乎是所有中央集权的决策系统的通病。愈喜欢乾纲独断的领导官员,就愈喜爱举国体制,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他最偏爱的项目上,除了显示其天纵英明外,也方便拍板的决策官员对国家资源上下其手。只要决策领导喜欢,自有幕僚与趋炎附势的谋士大加鼓吹,数十年来因此出的糊涂政策也不在少数。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类官场简单化的官场思维也随处可见,举国体制的做法也从未断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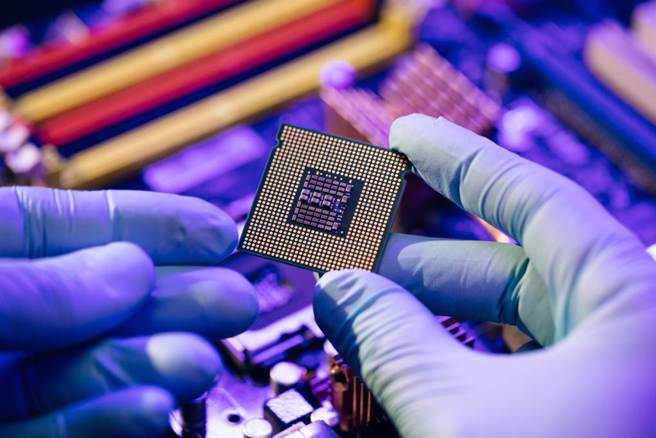
据称这次有政策幕僚提出对某些科技攻关项目採用举国体制,是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晶片与科学法》,这很可能是误传,毕竟举国体制的思维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断绝过。从中国想要追赶与西方科技落差时,就经常使用举国体制思维来进行技术攻关,直到现在遭到科技禁运,更是言必称「氢弹与光刻机哪个比困难?」这次在中共中央深化改革会议再提出「新型举国体制」,从媒体上查询所得,最近明确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大陆半导体市场讯息公司芯谋研究的首席分析师顾文军。他在研究报告中公开指出,晶片法案生效后会形成虹吸效应,中国晶片行业寻找确定性,应对之道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全局。

诚如许多专家所言,举国体制并非灵丹妙药,它很多时候反而是一帖仅为迎合集权体制官僚思维的毒药。过去它在某些特定时空确实曾经奏效,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做法仅能适用于一些没有或极少竞争的项目,而且必须是不必经过市场验证具有利基的项目。因为举国体制下不计代价进行攻关,结果通常会花费大量资源,研发出来的产品因为成本太高而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简言之,搞同归于尽的末日武器可以,要做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的商品就不行。

在过去以举国体制大规模投入半导体开发的经验上,中国没有少吃过亏。远的有武汉弘芯、成都格芯等10大半导体烂尾工程,近的有紫光集团与集成电路大基金,从百亿级别一直亏到数千亿人民币级别,规模愈大只能是效率愈差、亏得愈凶、公司领导层贪腐愈严重罢了。现在又提出「新型」举国体制,外界还不知「新」在哪里,但摆明了要用举国体制来进行晶片技术攻关,证明它仍然是20多年来的旧思维。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