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个人个性强烈发展的时代,服膺「赖活不如好死」的生命原则,这样的信念何以被后世遗忘?战国,是战争规模持续升级的时代,富国强兵是国君放不下的目标、人民躲不掉的日常,又如何衍生歷史诠释权争夺的现象?
雄辩,是战国的风格标志。墨家以「天志」保证兼爱;孟子让「仁义」在战国现实中还有用武之地;荀子讲「礼」的约束训练;国际秩序则取决于纵横家的穿梭游说;而在南方的楚文化,神话与异界交织的环境里,还有个书写个人极端情绪的屈原。最后胜出的法家,靠的是现实示范,由此建立「绝对王权」的起点。
秦朝是个早熟的帝国。抗拒死亡、相信久长,是秦始皇的执念;雷厉执行一统、重今贱古,是秦始皇的野心。但法家的「轻罪重罚」,形成庞大的刑徒部队,竟成为秦帝国快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精彩书摘】
从歷史的角度看,秦所建立的这个大一统帝国,有着概念想法和实践执行上的一定落差。几百年的「共斗不休」,无法建立有效的列国和平并存秩序,迫使秦彻底改弦更张,放弃周代分权式的政治安排,转为中央集权。然而要由中央来掌控那么大的土地、那么多的人口,具体所需的条件,即硬体和软体的条件,其实都尚未成熟。
这是一个「早熟」的帝国。「早熟」意味着缺乏许多有效地让这样庞大帝国运作的环节,因而产生了内在的诸多问题与困难。这些问题与困难,很多和皇帝本身的能力无关,而是源自制度本身的缺失。或者换一个方向说,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缺失,得靠极有能力的皇帝才有办法真正运作起这个大体系,现实中绝大部分一般、平庸,甚至不及平庸的皇帝,就只能坐视大体系的堕落、崩坏了。
法家将整个社会打平,取消自然多元及层级的做法,绝对不是最理想的。违背自然人性,将一套固定的模式强加在天差地别的地域与人群上,必然引发各式各样的后遗症。然而在战国末年,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从儒家、道家到名家、阴阳家,给的都只是理论,不是实际的制度。在执行的制度面,法家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
对比西方十八世纪最热闹的政体讨论就明白了。欧洲当时也想要找出取代没落、僵化封建王权的制度,在讨论中互较长短的,都有自己的一幅蓝图,从彻底的集权到彻底的民主分权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认真思考并进行细节规划。那是一个真正热闹的政治意见竞技场,逼着每一种立场的人都要有具体制度与改革程序的规划。
相对地,虽然我们也用「政治思想」的概念去整理春秋战国的各家思想和论理(例如萧公权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但这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多具体制度设计上的想法。真正落实到制度面的只有法家。
法家将国君的权力不断往上抬,抬到近乎绝对的地步,皇帝的「诏」、「令」就成了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则,高于包括传统「礼」在内的一切规范,如果不遵守就会遭到严苛的惩罚。这样的安排,和儒、道等各家的态度相反。其他各家的出发点是寻找真理,寻找一套普遍的原则,期冀依照找到的真理、原则去建构起现实秩序。法家不只跳过了抽象真理、原则的讨论,还反过来从现实出发,先建立起国君的绝对地位,然后让国君、后来的皇帝来决定真理。皇帝就是真理的最终依据。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这是泰山刻石的内容,也是秦始皇巡行刻石上典型的字句,表明了皇帝即位制定种种制度,皇帝就是一切的权衡,皇帝决定了一切事物的「法式」。琅琊刻石也说:「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由皇帝诏令所构成的「法度」,是「万物之纪」,决定了人世间所有的关系规范。
这是对皇帝地位的最高推崇,皇帝不只在权力所构成的秩序中心,这整套秩序就是他建造起来的,他就是真理中心。不是说皇帝所言所行都符合真理,而是皇帝的所言所行就是真理。
这样的新秩序中,皇帝当然不会错、不能错。这是扭曲且专断的决定,必然带来许多严重的后遗症。在没有其他现实主张对手的情况下,法家的论点迅速升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法家所构想的,是一套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完整周密的制度,像是许多零件没有组好就上路的车。状况好、运气好、驾驶的技术也好时,这辆车或许可以顺利跑上一百公里。然而只要状况、运气、驾驶技术稍有差池,车就开始逐步解体了。再跑一段距离,终会到车体散开、不得不重组的地步。
两条没走的路,两个错失的机会
战国长期混乱之后,换来了一个庞大、早熟的帝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过让列国可以和平共存的秩序。这是一条没走的路。另外还有一条没走的路,是由吕不韦所编撰的《吕氏春秋》所呈现的。
吕不韦势力最盛时,集合了眾多门客,编出一大本《吕氏春秋》,那是类似百科全书般的书籍。换句话说,《吕氏春秋》在基本用意上,和战国时期的其他书籍大异其趣。百家争鸣时,写书留下记录的第一项前提就是表明家派立场,为了将自己的家派和特定的立场说得更清楚、更强烈,才诉诸于着述手段。然而《吕氏春秋》挂了「吕氏」二字,是吕不韦的名字,但「吕氏」不是一「家」,也不属于任何「家」。
《吕氏春秋》要将各家各派的说法齐集在一起,形成一部大百科,将这些过去不同来歷、彼此争执的知识与主张整合起来。《吕氏春秋》的表面结构,用的是月令季节自然循环变化,接近道家;碰触自然规律时,用的是阴阳家的概念;但从自然联繫到人文现象时,又明显偏向儒家。而《吕氏春秋》产生于法家大本营─秦国,其中当然也会有许多法家的成分;当谈到社会安排时,又掺入了一些来自墨家的影响。
从比较负面的角度看,这像是个大杂烩,什么都拉进来;但从比较正面的角度看,这样的取径应该有其更深刻的意义。徐復观先生就认为,《吕氏春秋》的内容不单是贪多炫耀,内在其实有着一份创建大融合系统的严肃用心。这是还来不及充分消化的一个诸子百家初步synthesis(综合体)。
同样是因应渴求秩序的时代背景,《吕氏春秋》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可能,不是把法家抬到最高,压倒甚至取消其他各家,而是建立一个较大的框架,尽量兼容并蓄,让各家主张在这个框架下互相折衷,最后产生出每一家都有一点的新体系、新秩序。
因为秦国的内部斗争,吕不韦垮臺了,换上李斯当权。不要小看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从《吕氏春秋》明白看出,吕不韦的政治视野是整合式的、包纳性的。但换成李斯,却抱持着近乎绝对的法家立场,要取消其他各家意见,取消法家态度以外的任何异质空间。如果吕不韦没有失势,如果吕不韦在秦统一的过程中有更大的掌控权,他的综合主义路线应该会让秦出现很不一样的政治运作,也让后来的中国歷史呈现很不一样的面貌。
宏观来看,这两条没走的路就是两个错失了的机会。也就是说,中国在西元前第三世纪出现了皇帝一人专制的帝国系统不是必然的,不应该被视为唯一的可能,更不能被解释为内在于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不可改变的命运。所有歷史变化的发展,一定有其偶然机遇,一定存在着现实以外的其他可能性。
(本文摘自 《不一样的中国史3:从争战到霸权,信念激辩的时代──春秋战国、秦》/远流出版)
【作者简介】
杨照
本名李明骏,1963年生,臺湾大学歷史系毕业,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
擅长将繁复的概念与厚重的知识,化为浅显易懂的故事,写作经常旁徵博引,在学院经典与新闻掌故间左右逢源,字里行间洋溢人文精神,并流露其文学情怀。近年来累积大量评论文字,以公共态度探讨公共议题,树立公共知识份子的形象与标竿。
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臺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新新闻》周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等职;现为「新匯流基金会」董事长,BRAVO FM91.3电台「阅读音乐」、臺北电台「杨照说书」节目主持人,并固定在「诚品讲堂」、「敏隆讲堂」、「趋势讲堂」及「艺集讲堂」开设长期课程。着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文学文化评论集、现代经典细读等着作数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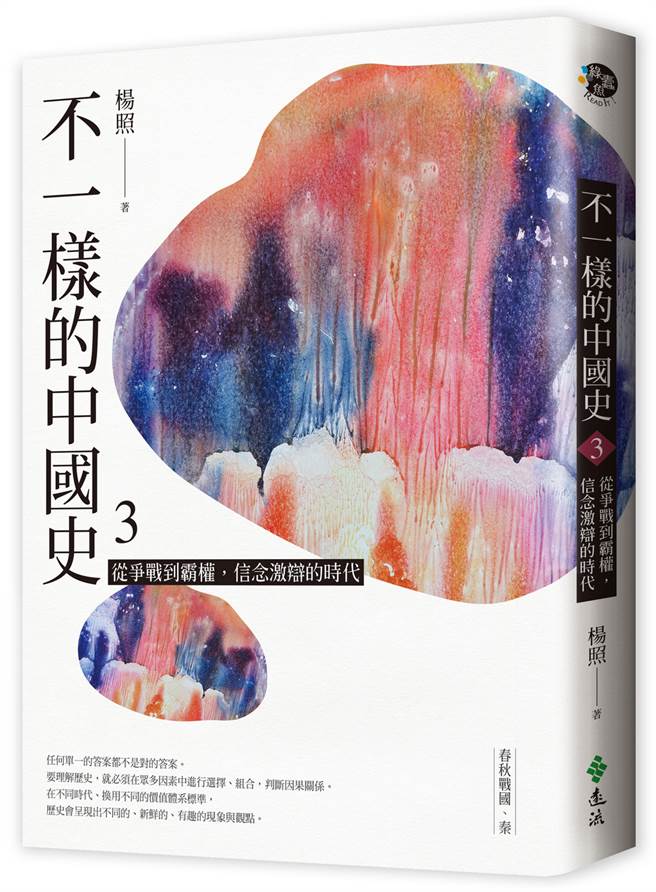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