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个人个性强烈发展的时代,服膺「赖活不如好死」的生命原则,这样的信念何以被后世遗忘?战国,是战争规模持续升级的时代,富国强兵是国君放不下的目标、人民躲不掉的日常,又如何衍生歷史诠释权争夺的现象?
雄辩,是战国的风格标志。墨家以「天志」保证兼爱;孟子让「仁义」在战国现实中还有用武之地;荀子讲「礼」的约束训练;国际秩序则取决于纵横家的穿梭游说;而在南方的楚文化,神话与异界交织的环境里,还有个书写个人极端情绪的屈原。最后胜出的法家,靠的是现实示范,由此建立「绝对王权」的起点。
秦朝是个早熟的帝国。抗拒死亡、相信久长,是秦始皇的执念;雷厉执行一统、重今贱古,是秦始皇的野心。但法家的「轻罪重罚」,形成庞大的刑徒部队,竟成为秦帝国快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精彩书摘】
法家提出用「法」来解决世乱,打掉封建的身分差异,以「法」一律平等对待。然而这套主张无法处理「法」的来源,或说「法」的根本权威效力来源的问题。法怎么来的?法要如何让所有人都遵守?法是商鞅订的,但法的权威不是来自商鞅,而是出于秦孝公,出于国君。国君的权力才是法的保障,如此一来,很明显的,国君高于法,法限制不了、管辖不了国君。
有一本记录毛泽东晚年权力与生活的书,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是长期在毛身边、担任毛的私人医生的李志绥。李志绥回忆,那个年代,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日,所有高干都要出席盛大仪式,但谁都没有把握毛会不会参加典礼。有时候毛睡晚了,他就不去参加了。
这是毛泽东超越其他人所享有的最高权力,他高过那些别人都要遵行、配合的党与国家的仪式。那个年代,毛搭火车出行,不只所有火车都要让毛的车先走,如果毛要在火车上睡觉,他搭的车要停下来,会从他火车旁边经过的班车也通通都要停下来。整个系统停摆,只等他睡个觉,没人知道什么时候火车可以再开,只能看他什么时候睡醒。
典礼他不配合,铁路时刻表他不管,甚至连自己订定的法令他也不遵守。在中国「一面倒」向苏联倾斜、冷战中敌视美国的时代,国家政策规定所有人要学俄语时,毛在做什么?他积极地在学英文、读英文书啊!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他在享受自己高于政策、高于法律的特殊地位、唯一地位。就连他自己订下的制度、法令,可以约束限制所有人,却不能约束他。他的主观意志高于这些固定形成的制度、法令,用这种方式凸显制度、法令来自他。
当规则、法令的权威来自一个人,要如何将这个人也纳入规范里?他要证明他是法背后的权威来源时,最清楚的做法就是让自己成为例外。管你们的管不到我,因为是我来决定怎么管你们,不能倒过来用我管你们的办法来限制我、管我。权力者往往是法的例外,藉由破坏法、不遵守法来彰显自己的权力地位。
因应这个根本的问题,而有了后期法家理论的重要发展。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包括慎到、申不害和韩非。一般传统的说法,商鞅是「重法派」,慎到是「重势派」,申不害是「重术派」,而韩非子是「集大成派」。放回歷史变化的脉络中,这几派其实不适合这样平行并列,各派间有彼此牵连对照的更复杂关系。
比商鞅晚起的「重势派」和「重术派」,其论理主要落在处理法的权威和国君权力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出发点就在于如何避免再度发生因为侵犯国君王权,导致立法者商鞅被秦惠文君诛杀的惨剧。对待国君和法这两种权力,「重势派」和「重术派」所强调的其实是彻底相反的。
慎到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站在法的这一边。慎到主张,国君想要最有效地运用法来统治,就应该将自己的「势」高高撑起,「势」抬得愈高愈好。用「势」将国君和所有人区分开来,表明了国君就是法的至高无上权威来源,国君的「势」愈高,法的权威相应也愈高。而国君的「势」要高到什么程度?怎样才是理想上「重势」统治的方法?国君要高到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不能有一点一样的地方,国君还要取消自己主观干预法、以个人意志进行统治的欲望。
在这里,慎到的重势派和《老子》的主张有了微妙的交集。慎到也主张国君应该「静默无为」,而他的理由是,一来国君「静默无为」才能「任法自为」;二来国君有作为就有可能犯错,国君主观决定所产生的错误,都会伤害原本高高在上的「势」,连带破坏了法的权威。
国君应该就坐在由各种「势」抬到超越至高的地位上,单纯扮演法的权威来源就好。要做任何事都得透过法,如此取消了个人主观自我意志,也就避开了个人犯错的可能性,使得别人无法反对你、侵犯你。说得更明白些,慎到主张,对国君最好、最有利的选择,是将自己彻底「非人化」,变成一个接受崇拜、膜拜的神像,从至高的地位上立法,透过法来统治,就没有人能反对你了。
在国君的角色,尤其国君和法的关系上,申不害的主张和慎到的形成强烈对比。申不害讲的「术」,关键在「莫测」。法是固定的,君王的统治术却要刻意维持不确定。慎到要以「势」让国君和臣子之间拉开无法亲近的距离,目的是不以国君的私人主观意志干预法,「任法自为」,臣子只要依照法行事,也只能依照法行事。申不害也主张国君不要轻易让臣子亲近,但目的完全不一样,是为了使臣子捉摸不定国君的好恶习惯,必须随时战战兢兢地揣测、讨好。
重术派强调的是国君作为法的来源的权威,将这种权威绝对化。有固定的法,人人依法行事,就不需要害怕国君,反正我不犯法就好,如此国君的权威就下降了。要维持国君的权威,连带维持法的权威,那就要以「术」将所有人保持在惴惴不安的状态中,随时警觉害怕。
重术派动用的一种「术」,和法家起源的原则刚好相反。国君手上最大的权力是赏罚。商鞅努力建立「信赏必罚」的原则,慎到把国君抬得高高的,高到不会去干预、改变法所规定的赏罚;申不害却教国君要「赏罚难测」。国君的赏罚没有固定模式,臣子就无从依照模式测探、掌握国君,国君拥有近乎绝对的自由,相对地,臣子被国君完全控制,没有任何一点自由。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 Hegel, 1770-1831)对东方专制的批评,根本上就是重术派主张造成的结果。「术」到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使得中国政治长期笼罩在人为的任意性中,无法制度化。潜藏着真正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性格的,其实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法家,而是这样的重术派,将「术」加入法中,因而破坏了法的客观性主张。
汉继承秦,也就继承了一个以法为主轴的帝国体制。汉代新的皇帝不了解法,也没有一套管理帝国的新方法,于是选择对秦体制概括接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汉承秦弊」,在「无为」中保留了秦代的制度。因而汉代的内在基本精神其实是法家的,一直到汉武帝时,才找出新的儒家加上阴阳的道理附丽其上,而有了「外儒内法」的局面。这种骨子里的法家,对中国歷史影响极其深远。牟宗三先生喜欢夸张地说:中国歷来所有的皇帝都是法家的,不管身边用了多少位儒家宰相,都改不了皇帝法家权力的本质。这话虽然夸张,但点出了不容忽略的部分事实。
需要稍加分疏的是,中国帝王的这种法家个性来自后期法家,尤其是经过了重术派衝击、补充后的法家,而非前期法家。
(本文摘自 《不一样的中国史3:从争战到霸权,信念激辩的时代──春秋战国、秦》/远流出版)
【作者简介】
杨照
本名李明骏,1963年生,臺湾大学歷史系毕业,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
擅长将繁复的概念与厚重的知识,化为浅显易懂的故事,写作经常旁徵博引,在学院经典与新闻掌故间左右逢源,字里行间洋溢人文精神,并流露其文学情怀。近年来累积大量评论文字,以公共态度探讨公共议题,树立公共知识份子的形象与标竿。
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臺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新新闻》周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等职;现为「新匯流基金会」董事长,BRAVO FM91.3电台「阅读音乐」、臺北电台「杨照说书」节目主持人,并固定在「诚品讲堂」、「敏隆讲堂」、「趋势讲堂」及「艺集讲堂」开设长期课程。着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文学文化评论集、现代经典细读等着作数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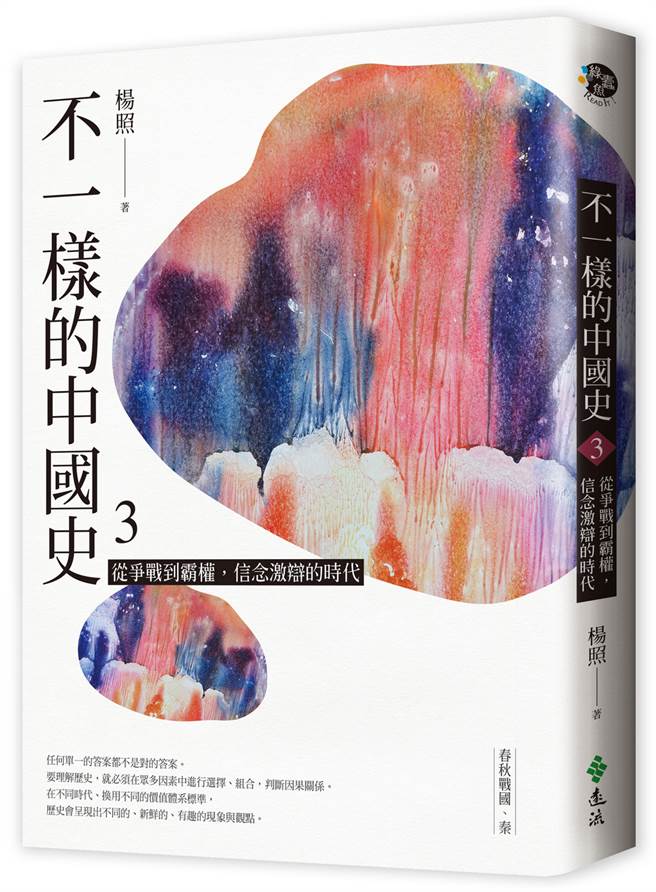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