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曾拜访过一位朋友家,他的家像书上的画;窗外有条涓涓长河,远方山景灰濛,树影绒绒,高耸绿木差点就伸入屋内。阳光将客厅照得透亮,经常是一个下午围坐沙发听着流水摩擦声聊着聊着就这样抵达黑夜。
自小对房子就有着奇妙的憧憬。
幼时栖居于都会区的透天宅,楼下是父亲经营的公司,在热闹的商业骑楼里度过童年极为特别。然而,身处流动的车水马龙声里,邻居们俱是巍峨耸矗的办公大楼,明明是所谓的高房价地段,家显得异常突兀,怎么就羡慕起屋后街衢的朽老公寓;想像着栖居巷道的静谧人家自厨房里端出一碟家常,像从文学小说里走出,飘散着微渺的香气。
在父亲事业衰败离世后,我与家人迁至市郊租屋。初次惊喜地抚触到住宅的样貌;笔直宽阔的中庭二侧莳满了葱郁株植,银灰色地砖闪过孩子们的譁然笑声,电梯框格般由缆线缓缓降下。房子大而明亮,弧形玻璃窗像天幕不断掷入充沛光线,不再是匿于商业区里的喧嚣与歧异感。但画面总停伫于母亲孤坐看电视。那时我才知晓,在父亲缺席后家是怎么绊绊磕磕的走过。
母亲过世后家庭成员解散,我与男友在山上租房,对房子的想像又像花朵于焉绽开。
我恣意妆点屋室学习独立生活;粉刷白墙,更新窗帘,在客厅搁上米白沙发鹅黄立灯,将餐桌铺上长巾书册排满书房,于空荡的露臺植满香草株植。只身逛市场学习辨识蔬果鱼肉,查找书籍按图索骥生涩地做上一桌菜。
原来,房子可以用来道别过去。我也能拥有画里的小屋。
之后,我们结婚买房装修房屋。装修老屋学问深幽风格多样;有北欧风,工业风,乡村风,日式无印风……等。美学是视觉的魔术,像为饱经风霜的女子洗净脸庞披挂衣饰,而有时稍不留心就会变得浓妆艳抹浑身戴满名牌。简单点不行吗?然硬体终归只是外衣,房子与家,居住与生活永远是一线之隔,重点仍在内里的温度与酝酿氛围。
房子也有着一张脸;阳光和蔼的老人,日系宅居文青,时尚的内敛女子,身型肥硕的富大叔,嘻哈叛逆少年,如同对应着巷弄公寓,华厦里的小套房,白净高耸的城市高楼,巍峨大院豪邸,以漂流木堆砌的滨海小屋。选择居所像饮食般有着高度的自由,没有标准,只在于预算与喜恶。
我时常刻意搭车经过旧家。
自远方望向那栋闹区老屋;狭长楼梯艳红塑胶窄扶手一径延伸至四楼,忆起以往出门每每行经楼下办公室都感到彆扭羞赧,夜晚商业区静阒无人,这日夜迥异住宅公司新旧楼房的混合体有种人面兽身的奇幻感。而父亲的忙碌与风流跌宕,让这个家如弃守的蜂巢,家庭成员们各自紧闭蛰伏于自己的暗穴中。年少轻狂的我常是几句话就与敏感的母亲对峙,青春的忧郁似墙上扩散渲染的霉渍。每当夜晚,一楼铁门拉下泛出喀啦喀啦的剥落声,如竖起的一道栅栏;父亲仍为着疾病事业所苦,家人们亦溺于烦恼的深井,大家皆囚困于这座如围城的家。当法院拍卖信函袭来,那些争执衝撞伤害连同这摇摇欲坠的楼,崩塌粉化夷为记忆的碎片。
窗外的施工碰撞声,让我返回了现实。
天光渐次亮起,梦倏地自我脑中散开,阳光溶进屋内。落地窗,棕色亚麻长帘,温润木地板滑过我的眼,露臺的株植勾勒出千奇百怪的线条,屋子被厚重的深夜清洗为洁净无垢的体腔,以早晨的姿态与我对视。
恍然间,我在一幢幢屋宇里长大、老去。房子始终静默。它如温暖的子宫,安全之蛹,总是温柔地包容着我。隐蔽在此,无论晴雨飓风递嬗流转,它亲昵地陪我度过光晦起伏的每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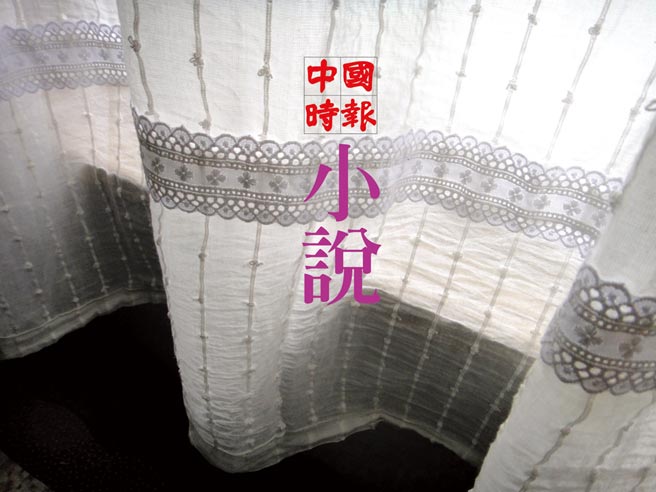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