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新朝有两项第一,未经流血衝突改朝之平顺,与前王朝断裂之巨大,都在中国朝代史上排名首位。新朝到底怪在哪里,又进行了哪些天翻地覆的大改造?
东汉承继西汉再起,表面上帝国运作模式一致,骨子里却与西汉有着根本差异。东汉皇后的角色与作用,显示东汉的统治结构变成了「大姓共治」,皇权空洞化之下,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外戚、宦官、士族的大乱斗?
以归零、新解的思维,扭转你过去所读的歷史印象,一套重新理解臺湾、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的书。
【精彩书摘】
中国文字持续使用超过三千年,在歷史研究和理解上,我们必须警觉的一个盲点是:看到同样的字词,很容易就视之为同样的事、同样的现象,而忽略了时移事往的诸多变化。
不过,持续使用的文字,尤其是中文这样的非表音文字,在歷史研究与理解上的方便好处远远大过障碍盲点。远在两千年前汉朝人的生活,保留在我们今天依然使用的文字中。文字是超越时空的密码,把汉朝人的生活包裹递送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得以立即掌握,甚至感到熟悉、亲切。世界其他文明大多缺乏如此悠久的文字系统,相对不容易有这样的好处。
举个例子,当下现实中,统一超商当红的商品是三角形的御饭糰,而统一超商在宣传御饭糰时,特别标榜使用的是臺湾本地产的「台粳九号」米。
「粳」这个字就是远从汉朝传下来的,它和另外两个字─「籼」和「糯」─一起构成了当时人对于米的基本分类和认识。三个字一组,指的是不同硬度的米:籼是最乾、最硬的,粳中等,糯则是最溼、最软的。
过去臺湾有「在来米」和「蓬莱米」。在来米就是一种「籼」,比较硬,很难煮熟。水加得少了,米粒感觉上没有水,很难咬;水加得多了,米会结成一块一块,看不到也吃不到粒粒分明的口感。因为难煮难吃,现在几乎没有人吃了,少量生产的在来米也都只供磨成米粉当原料。
到今天,用来做油饭、粽子的米,我们都还叫做「糯米」,以区别一般日常白米饭使用的「粳米」。只不过在汉代时,籼、粳、糯指的不是明确的米种分类,而是比较接近相对的硬度形容,口感上较硬的叫籼、较软的叫糯。
这一组名词会在汉代出现,显示了从战国到秦汉的饮食习惯变化,即米食的重要性提高了。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原本比较适合在南方生长,而在北方较为少见、稀有的稻米逐渐变得普遍,所以稻米从少数人的偶而享受,进入多数人的饮食生活中。累积了足够吃米的经验,才会在语言文字上予以正式分类记录。
因为水利灌溉的普及,稻米的生产区域往北移动,这个时代的文化核心区里,愈来愈多的人种米吃米,这是汉朝人生活的一个新现象。
肉食以猪肉为最,饮品以米浆为常
当时人使用的基本食材中,有一些至今保留在中国菜里。蔬菜类中有白菜,还有芹菜。芹菜又称水芹,原来是长在水边的野菜,这时候转型成为主要的种植菜类。另外,芥菜也很普遍。有竹子的地方,自然就有笋;种荷花的会採收菱角和莲藕。攀藤类植物中,葫芦也是很早就在中国主流食材范围内。
那个时代还有些食物,名字看起来很陌生。例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这是形容汶山土壤肥沃,住在那里永远不必担心会饿到。汶山出产什么,可以保人「至死不饥」?原来是一种叫做「蹲鸱」的东西,「鸱」是猫头鹰,「蹲鸱」传神地描述了它的模样:矮矮的、圆墩墩的,像窝起来的猫头鹰一样。那是什么?今天我们叫做「芋头」,它富含大量淀粉,是可以提供基础热量的根茎作物。这项食材现今仍在,但「蹲鸱」这个名字完全消失了。
在那个时代,北方的冬天基本上不长蔬菜,唯一的例外是冬葵。汉代的人经常吃冬葵,那是冬天仅有的调剂。但这样东西不知为何,从两晋以降就从中国人的饮食中淡出,或许和长期的天候变化有关。今天我们熟悉的只有秋葵,只能依此推想,冬葵和秋葵应该有一定程度的类似吧。
还有「鸡头米」,底下的叶子像荷叶,上面有果实,果实上长着细细的小刺,大概像栗子吧,但比栗子小。小小颗的鸡头米剥开来,里面是浅色的、珠玉般的小球。鸡头米后来在中国饮食史上的地位,还不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中国文学,尤其是色情文学中,「鸡头米」成了女性乳头的形容词,甚至是代词。
当时人吃的肉,主要有猪和鸡,这我们不意外。稍感意外的,是狗肉相当普遍,史书上出现好多杀狗的「狗屠」,吃狗肉的机会仅次于猪肉和鸡肉。此外,中国传统所谓的「六畜」,这时候已经明确出现猪从中脱颖而出的倾向。猪愈来愈重要,在汉朝,猪肉的普及程度和在饮食中的重要性,已经不是其他动物性肉类赶得上的。
环绕着猪肉产生的肉食文化,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在宋代以后的近世中国社会里,猪是唯一一种普遍进行专业养殖的肉类动物。相对地,鸡是农家在家户环境里养殖的,鸡和鸡蛋没有商品化,供应比较不稳定,也就相对比较珍贵。近世以降,供应最稳定、最容易取得的一直是猪肉,所以猪肉的吃法也最多。这种以猪肉为中心的饮食习惯,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考古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曾经记录和猪有关的内容,分类极为详细。其中一片汉简上写着:「头,六十。肝,五十。肺,六十。乳,二十。蹄,二十。舌,二十。胃,一百。髋,三十。心,三十。肠,四十。」这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份价目表。再从竹简的上下文推断,这应该是猪的价目表,因为竹简上另有一个项目指的是牛,另一个项目指的是鸡。牛和鸡都只列单一项目,猪却从头到其他部位、到内臟都分得那么仔细。这种买卖方式上的差异,清楚显示了猪的特殊地位。猪肝、猪肺、猪舌、猪肚、猪蹄……,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特殊的调理与食用方法,这也是猪食占据肉食中心位置的明证。
那个时代的人喝的东西,当然有酒。至少在一万年前,人类就发现了酿酒的方法,一路传下来,每个社会、每个文明都懂得以谷物或水果酿酒。
不过两汉时期有一种特别的饮料不能不提,那就是「浆」。两汉史料中经常出现「浆」,指的是米浆。但汉朝人喝的米浆也不是现在臺湾早餐店卖的那种。我们喝的米浆是先将米炒过、炒熟,甚至炒到有点焦,然后再磨再煮的,这样做出来的米浆呈现褐色,而且带有浓厚的焦香。
古代的米浆就是单纯用米煮的汁,顏色是白的。有时会混进一点麦,顏色变得没那么白;有时会加一点甜味,可能来自蜜。这是当时人最常喝的东西,不单纯当饮料喝,还是下午餐与餐之间最普遍的点心。那时候还没到吃饭时间若肚子饿了,就喝米浆,所以常在史料中看到「饮浆者」、「卖浆者」一类的字词称呼。
当时也已经开始喝茶,但还没发展出细腻且讲究的茶文化。另外,也吃一些树上长的果子。前面提到两种不同的「黄瓜」,那是从外地传来的胡瓜,比本地产的瓜果好吃。本地产的瓜果一般拿来解渴,而且被视为穷人的食物。那时的瓜果跟我们今天习惯吃的水果,吃起来很不一样。当时对瓜果的形容,一般都是硬、涩、乾,不像经过多少年改良后的现代水果那样软、滑、甜,且充满水分。因为不好吃,通常都是穷人或遇飢荒时才不得不吃的果实。如果连果子都吃完了,恐怕就得吃草或吃树皮了。
(本文摘自《不一样的中国史5:从清议到清谈,门第至上的时代──东汉、魏晋》远流出版)
【作者简介】
杨照
本名李明骏,1963年生,臺湾大学歷史系毕业,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
擅长将繁复的概念与厚重的知识,化为浅显易懂的故事,写作经常旁徵博引,在学院经典与新闻掌故间左右逢源,字里行间洋溢人文精神,并流露其文学情怀。近年来累积大量评论文字,以公共态度探讨公共议题,树立公共知识份子的形象与标竿。
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臺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新新闻》周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等职;现为「新匯流基金会」董事长, BRAVO FM91.3电台「阅读音乐」、臺北电台「杨照说书」节目主持人,并固定在「诚品讲堂」、「敏隆讲堂」、「趋势讲堂」及「艺集讲堂」开设长期课程。着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文学文化评论集、现代经典细读等着作数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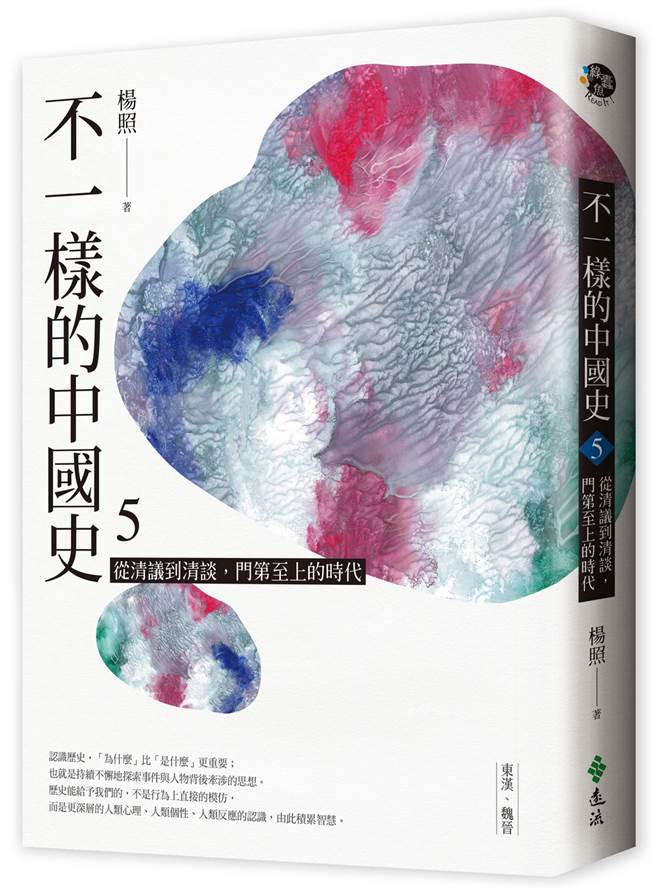

发表意见
中时新闻网对留言系统使用者发布的文字、图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权利。当使用者使用本网站留言服务时,表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规定:
违反上述规定者,中时新闻网有权删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锁帐号!请使用者在发言前,务必先阅读留言板规则,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