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6年7月國共在蘇北的大打,到10月間國軍進占張家口,為時3個月,是國共邊打邊談時期。共方的談判方式,則由消極的爭取停戰時間,進至積極備戰時期。其方式「堅持政協路線」,「把談判作為教育人民的工作」。亦即周恩來所謂:我們把對方不願解決問題,告訴人民,用以教育人民。使「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民主方針,與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方針」,經過談判,「為群眾所認識。」因此,「和平雖不可能,但為了教育人民,談判是必須的。」
同時,周氏也要第三方面人士得到教育,使他們懂得談判不會有結果,就同意他們去調解。因為他們內部的大部分人士很動搖,想來個折衷方案,解決問題,希求和平,不一定是聽共產黨的。
周氏這種談判方式,馬歇爾對葉劍英說:「周將軍(恩來)最近幾個月來(按:指7月到10月),並不是為談判而談判,而是為宣傳而談判。」
根據周恩來的分析,第三方面總是不斷的動搖,因為國方二陳(果夫、立夫)、陶希聖等,堅持要開國大。因此,第三方面就發生了分裂的局面,青年黨與民社黨參加國大,早在意中,張君勱(民盟中的民社黨)極端動搖,胡政之自稱內外夾攻、左右為難,黃炎培加上一句「天人交戰」。另外還有幾種人,如陳銘樞反蔣而不進步;黃炎培、章乃器等自有立場,不願投蔣,但動搖不定。同時第三方面也不斷新生,如聞一多、馬敘倫、馬寅初,學習求進步,聯繫群眾。同時,昆明、北平、上海都新生了第三方面的群眾領袖。因此,周之爭取動搖分子目的在教育群眾。
為何要以談判來教育群眾?依周恩來之說,要使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針與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方針被群眾所認識」,同時也要使「群眾對美覺悟」。因為抗戰初期,群眾對中共的認識,只重抗日,並認過去暴動政策為錯誤,他們到延安去,亦多自民族立場出發。現在則不同,「共產黨抓住獨立和平民主的旗幟,而與賣國內戰獨裁的國民黨相區別」。由抗戰初期左右之分,變為是非好壞之分。至於美國方面,因群眾對美幻想很大,但自中共6月、7月間發出聲明,指出「美國對華軍事援助的實質,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以及「蔣介石反動派繼續獨裁和內戰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反動派的軍事干涉」以後,「群眾對美覺悟,已普遍得出乎意外。」
這是「教民作戰」,預設「倒蔣」、「反美」的作戰目標。
周氏所謂的政協路線,也就是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路線,是他們長期的奮鬥目標。為什麼叫政協路線而不叫政協決議呢?周說:政協決議已被國方破壞,如果將來再談判,共方絕不承認過去的國大等等。所以決議可變,但路線不變,即黨派協商、共同綱領、聯合政府不能變。只要抓住這個路線,標榜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方針。而以武裝鬥爭為根本,用以戰勝蔣介石集團。
蔣在6月的談判失敗後,仍於7月2日找周恩來直接談判,談的最多的是蘇北問題,一再重複蘇北對南京的威脅,說這個問題解決以後,再談國大等問題,周沒有鬆口。當晚,周恩來約同王世杰、陳誠等再談這個問題,王承認按照在政協決定的原則,先改組政府,實施共同綱領,然後再解決有問題的地方政權,舉行民選。王說:政府對東北若干省,已允可暫時不照1月10日之停戰協定接收,中共對蘇北問題,必須讓步,周堅決不允,致無結果。
蔣氏顯然不願再拖下去,未與有關人員商量,即經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王世杰建議先確定召集辦法,再行宣告日期,希有緩衝日期,未被接受。
周恩來即向馬歇爾表示:11月12日召開國大很突然,等於政府又投下一顆炸彈。政府現在的作法,片面的召開國大,不願開政協,這不合乎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了。這和你(馬)初來的談話,政協協議以及杜魯門總統聲明的精神相違背。
此乃周氏「政協路線」的使用,用以綑綁國民黨也。同時,周恩來也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斐斐說:
美蘇關係的不好,常影響到中國的內政,這是事實。但從中國的立場看,並非沒有辦法可以自處了。如果國民黨的政府是聰明的話,它應該自動地負起橋樑的作用,不要甘心地作一國的工具。或許如果中國的國民政府改組成聯合政府了(按:照政協那樣去做),與一切盟國都保持友好關係,則中國不致完全受一國的影響,不能自拔,而且可以反過來積極影響國際間的合作。
周氏之言,雖是宣傳「政協路線」,卻完全像個自由主義者。人民聽了,定會很贊同;但也會覺得國民黨很不對。
【未完待續,蔣世安專欄每周四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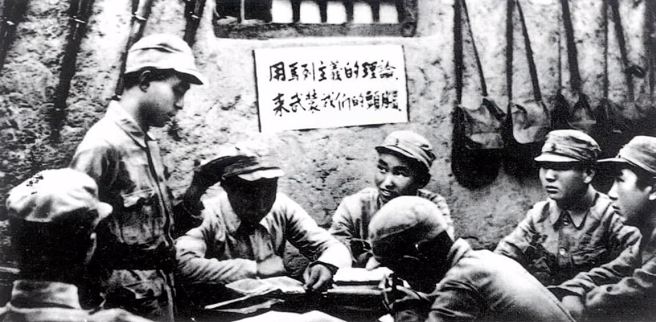
發表意見
中時新聞網對留言系統使用者發布的文字、圖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權利。當使用者使用本網站留言服務時,表示已詳細閱讀並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規定:
違反上述規定者,中時新聞網有權刪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鎖帳號!請使用者在發言前,務必先閱讀留言板規則,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