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生活便利,但沒有先人的努力就沒有現在的日子。知名歷史學家楊照透過《不一樣的中國史》,述說每個朝代的重要性,其中在華人最早出現的時代夏商周,原本僅是部落民族,靠著突破性的發明,開創強大的王朝;書中打趣地敘述考古學就是「挖死人骨頭」,也在過程中依稀看到村落遺址、陶器、青銅器和甲骨文等古文物,更見到夏商周時期部落相愛相殺的互動競爭。
【精彩書摘】
為什麼商人會耗費龐大的資源去鑄造青銅器?
青銅器的鑄造與器皿神聖性
商朝的青銅器形制很多,有鼎、鬲、甗、簋、釜、爵、角、斝等等,看得眼花撩亂。青銅的起源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在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由製陶技術產生了火窯;到了二里頭文化,出現了白陶這種特殊陶器。按照燒製溫度來排列,黑陶比彩陶所需的溫度來得高,白陶所需的溫度又比黑陶更高。大約要一千到一千兩百度的窯溫,才能燒製出白陶。所以一個地方出現白陶,也就意味著該地的火窯技術已經突破攝氏一千度。能在火窯裡燒到一千度、一千兩百度,泥土裡含藏的金屬礦物質也都會被熔出來。
我們可以合理想像,這個區域的人一旦發明了如此高溫的火窯技術,必然會在燒陶過程中看到各式各樣、極為新鮮的金屬現象。然後可能再花幾百年的不斷試驗,逐漸試出一種遠比陶器更穩定、更堅硬的材質。
商文化在這方面的表現很突出。發現青銅之後,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取代陶器。青銅的用途除了少量用於製造兵器外,絕大部分用於將原來的陶器改成青銅材質。從這個事實,我們可能得到的推論是:正因為青銅等金屬材質都是在燒陶過程中發現的,對當時的人來說──他們不像我們今天擁有這麼多知識和因果邏輯思考能力──很自然傾向於認為這種新的材料比陶器更堅硬,更適合拿來取代陶器。因為在製程中產生的親近性與聯想,使得青銅自然取代了陶器,用來製造許多承襲陶器功能的器皿。
在新石器時代,陶器的重要性來自它是水、火與穀類混合的重要處所(locale)。另一個合理的推測是,在遠古時代的人眼中,陶器應該像是具有神力的東西,可以將原本硬邦邦的東西化成方便可食、甚至好吃的食物,他們無法理解水與火在陶器那個環境中所起的變化,很容易就對這種容器產生魔法的想像。
隨著農業的起源與發展,中國很早就有把穀物變化的神奇作用歸因於器皿的想法。用今天的語彙來說,就是器皿取得了「宗教意義」,所以後來的人發現任何新的貴重材料,自然就會將貴重材料用在神奇的東西上,讓它更顯神奇。
這或許部分解釋了為何中國的青銅器很少真正運用到青銅硬度高的實用特性。即便看到商朝的青銅兵器,我們也不能理所當然就認定那是在戰場上打仗用的,它們有可能使用在儀式中。
鼎是商朝青銅器裡最普遍的形式,從它的形制和花紋,可以清楚了解青銅器的製造過程。從商到周,中國的青銅器除了少數例外,基本上都是用「範鑄」的方式做出來的。青銅與陶土、陶器有著密切關係。
先做一個器物模型,然後在模型外面做成「範」,一塊一塊接起來,將之包起來。也就是首先要用陶土燒出一個和青銅完成物一模一樣的東西,然後在這東西上面包覆一塊一塊也是陶土做的「範」。範做好後,把它拆開,移走裡面的模型,再重新組合起來,變成一套中空的範。接著往裡頭澆灌青銅汁,等到青銅汁冷卻,拆掉外面的範,就出現我們所看到的青銅器。
因此,青銅器的形制當然會受到「範鑄法」的限制。不過除了看到限制,我們更應該看到那個時代工藝技術與工藝設計發展到什麼樣的驚人程度。商朝青銅器的尺寸不會很大,然而用現代技術仔細復原製造過程,會發現其中的難處,就是它必須做極精密的設計,裡面的模子形狀必須先考慮到外面的「範」的築法。範要能一塊一塊切開來,還要能一塊一塊再拼回去,拼出沒有缺漏的樣子。這個需要極精巧的思考和極高度的空間邏輯能力,事先規劃清楚什麼形狀和什麼角度可以做,什麼形狀和什麼角度不能做。
除了中國之外,其他主要的青銅文明製造複雜的青銅器,最終都走上同一條路:脫蠟法。脫蠟法不像範鑄法那麼複雜。蠟在高溫下會融化,所以就先用蠟做出器物的樣子,在外面用泥巴包起來,然後點火,一方面將泥燒硬,一方面將蠟熔成液體,只要預留一個孔讓臘汁流出來,就能成功燒出中空模子。接著封填讓臘汁流出的洞,從另一個開口將青銅汁澆灌下去,等它冷卻、硬了,再打掉外面的模子,裡面那個青銅器就會長得和原本用臘做的器物一模一樣。顯然,用脫臘法做出來的形狀變化可能性大得多了。
中國大概有一千年的時間一直以範鑄法造青銅器,而沒有用脫臘法。我們可以確認中國很早就發現了蠟,但就是沒有將蠟應用在製造青銅器上。其中一種解釋是:青銅器如何製造的方法和過程,與製造出來的器物結果一樣重要。
青銅紋飾的通天地象徵
讓我們思考一件比較特殊的器物:有一只青銅盆,盆裡環繞了四條龍,更特別的地方是,它裡面刻有兩個像老虎的圖樣,張大了嘴巴,將一個人頭包在中間。完全一樣的圖形在一個大鉞(斧頭)上也刻著。另外還有幾個類似變形的例子,出現在不一樣的器物上。
這象徵什麼?代表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進一步認識一下青銅器上的紋飾。前面提過青銅器上紋飾的重要性,最主要的幾種紋飾有饕餮紋、夔紋、龍紋等等,幾乎所有紋飾的源頭都與動物有關,都是從動物的具象描繪加以變形抽象化。例如饕餮,一下子就看到像眼睛的形象。我們可以查到的古書文獻上說:饕餮指的是貪吃,饕餮和大吃、肉食都有密切關係。
以此推論,前面列舉的圖樣是在描述動物吃人嗎?表面上看來滿像的。但張光直先生做了不同的解釋,給了我們更寬廣的意義空間。他認為,青銅器上的紋飾彰顯了一種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我們想當然耳的威脅關係。
張光直先生的經典史著《美術、神話與祭祀》(Art, Myth, and Ritual)中,以文獻和考古巧妙且綿密的對照,主張饕餮紋所顯現的是人類如何藉由動物進出不同世界的神話。也就是說,青銅器上的紋飾與奇特的圖樣是在記錄並顯示,這些青銅器的主人擁有的神奇力量。這股神奇力量最主要的內容是,他或他們可以和一般人認為已經不存在的人進行交流。用現代說法來講,商朝人可以和靈異溝通,而他們跨界溝通最重要的對象是祖先。
透過後世文獻回頭重建商人的概念,他們似乎將存在的世界分成兩大塊,一塊是我們所生活的空間,另一塊是去世的祖宗所存在的領域。這有點像古希臘世界觀中,人和奧林帕斯山諸神有所區別卻又頻繁互動的架構。上面的那個領域隨時有能力,也隨時可以介入來改變下面的空間。
只不過,古希臘人想像的住在奧林帕斯山上的眾神,往往純粹出於任性而干預、改變人類的命運。很多希臘神話故事的重點都在讓人相信命運是無法違抗的,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然而,在商人的概念中,上下兩個領域卻有一套具體的互動秩序,最根本的互動原則就是:自家祖先保佑自家子孫,誰家的祖先在天上愈有權威,他的子孫在地上就愈有辦法。
如何證明這兩塊領域的存在?又如何讓別人感受到上面的領域中,商人的祖先勝過其他人的祖先,因而商人在世間理當該占有統治地位?要達到這樣的目的,一定要有兩塊領域間互相溝通的證據。
依照張光直先生的說法,青銅器之所以重要,因為它們都是禮器,都是儀式性的器物。每次一動用到這些青銅器,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讓所有人感知到,憑什麼你們要聽我的,就因為我背後有一個你們無法擁有與展示的更巨大超越的靈異力量。
商人以誇張的規模與方式,長期反覆地示範:我們商人和你們不一樣,雖然大家都有祖先,可是只有我們擁有隨時可以和祖先直接對話的管道。透過這些你們無從擁有的青銅神器,青銅神器上還有可以通天地、上下往返的神獸,我可以直接召喚我們的祖先,請他們降靈來協助。這就是後來周人所說的「神道設教」[註1]。
張光直先生的洞見至少說明了幾件事情:第一,為什麼商人會耗費這麼龐大的資源去鑄造青銅器;第二,為什麼青銅器都是禮器,而沒有實用工具;第三,為什麼青銅器上普遍有複雜的紋飾,而且紋飾和動物關係密切;第四,為什麼就算到後來出現了文字記錄,人們還是給像鼎這樣的青銅器那麼高的象徵地位。
更關鍵的是,透過張光直先生的說法,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商朝集中資源的運作模式。
商人掌握了巨大的威嚇優勢,他們宣稱並示範自己可以透過一個神祕巨獸張大的嘴巴上到另一個世界,將超越的力量召喚出來。於是,那些沒有這種本事可以通天地、進出另一個世界的人只能乖乖聽話,乖乖依商人安排的方式奉獻生產所得,如此造成了資源的高度集中。
(本文摘自 楊照《不一樣的中國史1:從聚落到國家,鬼器森森的時代───夏、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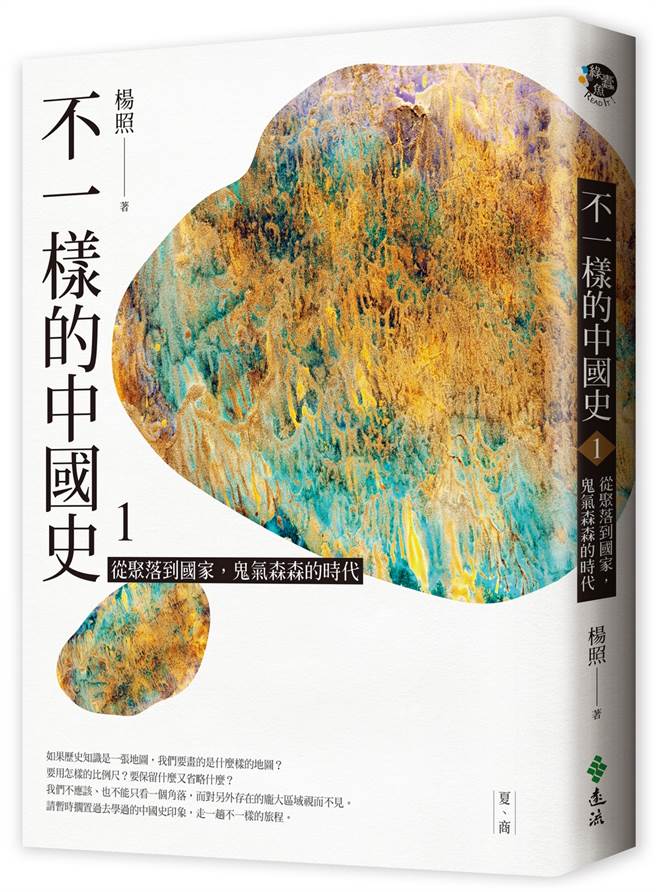

發表意見
中時新聞網對留言系統使用者發布的文字、圖片或檔案保有片面修改或移除的權利。當使用者使用本網站留言服務時,表示已詳細閱讀並完全了解,且同意配合下述規定:
違反上述規定者,中時新聞網有權刪除留言,或者直接封鎖帳號!請使用者在發言前,務必先閱讀留言板規則,謝謝配合。